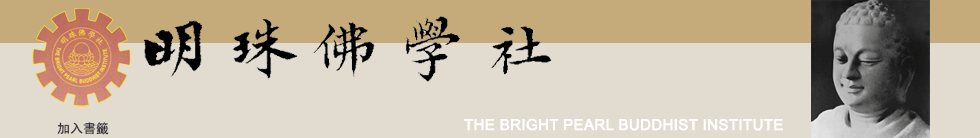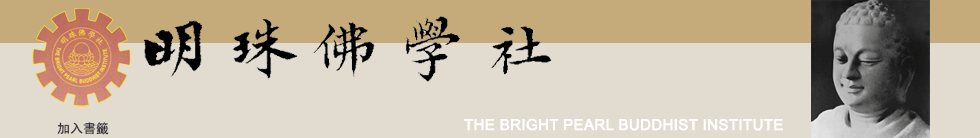第八屆經論研習班(2000 – 2002年度) 修業報告
學員:陳啟賢
試釋《六祖壇經》中「無念為宗、無相為體、無住為本」之大意,兼論六祖禪宗的源流和特色。
當學生接獲這題目時,嘗與友人討論,朋友打趣說,這還不簡單,交一張白紙,勝過千言萬語。確然,禪法不在論而在悟,但弟子畢竟是凡人,未可期見道之日,故一再閱讀《壇經》,並參考其他資料,發現六祖的「無念、無相、無住」不獨是其禪法宗旨,融合空有(這裡指「佛性」,而非「唯識」)二宗,並開創了中國佛教的新方向,殊不簡單。要了解「三無」,當探本尋源,一面從禪宗的發展與融合中國文化來看,一面則從如來藏與空宗入路,理解六祖的「自性」與般若思想的關係,故加上「兼論六祖禪宗的源流和特色」這副題,作較宏觀的探討。
從禪坐到禪宗
禪,本為梵文「禪那」( Dhynna )的簡譯,意為「靜慮」、「思惟修」。早於釋迦成佛前,印度人已經坐禪,在樹蔭下苦思生死問題,或於定中體會梵我合一,提昇精神境界。可見坐禪是一種修行的形式,從《梨俱吠陀》到《奧義書》時代,坐禪已流行於各宗派。原始佛教的戒、定、慧三學中的定,就是指坐禪。「同檯吃飯,各自修行」,釋迦所倡的內觀禪,殊異於外道,不單「止」,還要「觀」,即不以住在「定境」為目的,而透過不斷的「觀」,通向體會三法印,趣向解脫。如是,從原始佛教以降,佛弟子皆通過禪,體會定、慧,並開出諸種觀法,如不淨觀、慈悲觀、緣起觀、界差別觀、數息觀等、以對治各類執著,所謂「由戒入定,由定發慧」,就是佛教徒修行三學的整體關係。然而,由於眾人意趣不同,在傳法的過程中,往往會強調其中一部份,尤在佛教分裂成部派之後,對法,對戒的解釋,各取一端,名相紛陳,所環繞的,就是佛陀究竟「說」了什麼,「教」了什麼的問題。
《金剛經》云:「『須菩提!於意云何?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?如來有所說法耶?』須菩提言:『如我解佛所說義,無有定法,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,亦無有定法,如來可說。』」又說:「『須菩提!於意云何?如來有所說法不?』須菩提白佛言:『世尊!如來無所說。』」
如來有沒有說法?如來不是啞吧,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,當然會說。釋迦住世,說法凡四十五年,隨眾生根器,循循施教。《壇經(宗寶本).般若品》云:「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,大小二乘十二部經,皆因人置,因智慧性,方能建立。若無世人,一切萬法,本自不有。故知萬法,本自人興。一切經書,因人說有。」各人悟性不同,施教方式雖然有別,但一言以蔽之,佛陀所指示的,就是一條破執、解脫之路。至於教法,本無定相,隨緣而施,是種種「施設」,三藏十二部,都可視為一套「臨時課程」,其功能就像《中阿含經》「筏舟喻」的小艇一樣(用完即棄)。但部派佛教徒則著著計較於章句,執「我空法有」,與佛陀的「破執」本懷,漸行漸遠,遂致大乘運動興起,龍樹菩薩宏揚「空宗」,蕩相遣執,諸部般若經常指出的,都是「緣起性空」,破名相、破二邊的中道。
可是,人的認知模式,總有局限。從佛教角度來看,無始以來,眾生均因無明而輪迴六道。無明,即不明緣起,不諳因果,形成種種執見,對世間法,甚至佛法也沒有例外。凡夫對經典的一字一句,愈奉為金科玉律,愈造成概念上的執著。另外,從科學角度而言,人對世界的理解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關係上,由孩啼時期開始,無論父母親人或一草一木,都是存在於自身以外的「客體」,通過這種認知所累積的新知識、新思想,都不過是納入「可理解範圍」的新內容,而理解得愈「清楚」,就愈有「安全感」,愈有「立場」。
為了對應以上的思維局限(執著),佛經不厭其煩地提醒大家,莫執於法,所謂「法尚應捨,何況非法」(《金剛經》)。但經典到底是文字,始終要解釋,而且一旦述及「終極」、「究竟」、「第一義」這些概念時,往往詞不達意,所謂「不可思議」,因為一旦想起,便會落入新的執著。誠如《維摩經.入不二法門品》所述,最高真理非但是文殊師利咀裡說的「無言無說,無示無識,離諸問答」,而是維摩居士那切切實實的「默然無言」。到底有沒有離文字,離名相而傳法的途徑呢?
《五燈會元.卷一》曾經提到,在靈鷲山法會時,佛陀接過大梵天王所獻的蓮花之後,高高舉起,弟子們莫明其妙,唯有大迦葉尊者默默報以一笑,釋尊說:「吾有正法眼藏,涅槃妙心,實相無相,微妙法門,不立文字,教外別傳,付囑摩訶迦葉。」這典故所流傳的,就是禪宗「拈花微笑」,「以心印心」的法門,亦是離文字相而體會佛陀解脫精神的原形。所謂「心印」,就是直接體會。周裕鍇的《禪宗語言》說得很明白:「佛教所言『心』是純粹的內在體驗,無法用言辭解說或文字傳達,這不僅因為體驗是非思維的精神活動,無邏輯可言……而且是純粹個人化的行為和成果 ……語言是思維的產物,是規範化、形式化的東西,而人的體驗卻是無限定、非規範化的形態,因此語言在表達人的體驗方面是無能為力的。」(註1) 而禪宗,就是在傳統依據經律論三藏來「理解」佛教之外,另闢一條直接體驗解脫精神的途徑,即「教外別傳,不立文字」,其施教原則重視實踐多於理論,上承原始佛教精神。然而,禪宗雖不立文字,卻不排斥經典,而視它們為成就「心印」的媒介之一,換句話說,就是不著於文字,不以字面解釋為究竟。
所以禪宗初祖達摩西來,亦以《楞伽經》傳法。相傳他見梁武帝,未能投緣,便轉至少林寺面壁九年,修「凝住壁觀」,並傳法予二祖慧可、慧可傳給三祖僧璨、僧璨再傳至四祖道信、道信傳至五祖弘忍、弘忍再傳至六祖慧能。禪宗由達摩的頭陀行到五祖的東山法門;由本於《楞伽經》到本於《金剛經》,經歷了頗長的融攝空有二宗、貫通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、叢林化和世俗化的過程。
引農入佛 另起爐灶
佛教自漢代開始東傳,雖然連綿不絕,卻沒有系統,大小乘經典往往同時出現。在禪宗興起前,中國佛教對禪的認識,如早期安世高的「安般守意禪」(小乘)、支婁迦讖的「般若三昧禪」和「首楞嚴三昧禪」(大乘)、鳩摩羅什的「大乘菩薩禪」,雖在目標上互不相同(小乘者趣向體驗三法印,大乘則趣向般若),但在實踐上,仍不離觀呼吸、觀四念住、觀諸佛形相,以求集中意志的「定學」法門,達致一心不亂。此說在崇尚道教的魏晉時期,與達摩初傳禪法,分為「行入、理入」二門。「理入」方面,所本的《楞伽經》,雖屬「如來藏」一系,但在施教上卻不拘形式,標出「藉教悟宗」之路。《楞伽經》云:「佛告大慧:一切聲聞、緣覺、菩薩,有二種通相,謂宗通及說通。大慧,宗通者,謂緣自得勝進相,遠離言說、文字、妄想、趨無漏界自覺地自相,遠離一切虛妄覺想,降伏眾魔,緣自覺趨光明暉發。是名宗通相。」(註3)換句話來說,「宗通」就是憑自證、自覺的直接體驗。「云何說通相?謂說九部種種教法,離異不異、有無等相,以巧方便,隨順眾生,如應說法,令得度脫。是名說通相。」(註4)可見「說通」就是不拘一格,多元靈活的教法。
「行入」方面,他修的「凝住壁觀」,雖然印度色彩濃厚,意趣卻近空宗。洪修平在《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》指出:「就壁觀在印度禪法中的本意來說,確實是以牆之土色為觀想的對象,並進而在幻覺中視天地為一色,以達到心地清淨的一種方法……但是,既然壁觀的目的在於使心地清淨,那麼就禪修的結果而言,壁觀即「心如牆壁「之觀法,亦不失其原義。事實上,「如是安心,謂壁觀也」,達摩來傳壁觀之法所強調的也就是「安心」……而突出「安心」,這是受大乘般若學與心性說影響的結果。般若非有非無,離言掃相,破除妄執,以無所得心,無分別智,證悟諸法實相,達摩以此來指導壁觀禪法……」(註5)可見禪宗自達摩開始,已傾向融匯空宗和「如來藏」思想,以般若思想為本、以心注一境的壁觀為用,以自悟為最終目標。在老莊玄學和涅槃思想當道的年代,這些創見不易為人接受,禪宗要在中國植根,需要如何調整呢?
援佛於道 裡應外合
印順在《中國禪宗史》扼要地說:「會昌(唐武宗會昌五年的「會昌滅佛」)以下的中國禪宗,是達摩禪的中國化,主要是老莊化,玄學化」(註6)。中華文化自漢以來,入世本於儒,出世本於道,「無為」、「清淨」這些概念早已深入民心。佛法初起,為了消弭文化隔膜和便於翻譯,自然借用老莊,方便弘法。這情況與佛教在印度發端時,吸納婆羅門諸神為護法以爭取徒眾大同小異。魏晉時,不少學者由道入佛,而佛教借用道家思想以弘法,並非始於禪宗。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在出家前,已然「愛好玄微,每以老莊為心要」(註7),後鑑於道家還未究竟而轉學佛,與他同時的廬山慧遠經歷相似。僧肇於《寶藏論》談到涅槃實相時說:「空可空,非真空,色可色,非真色。真色無形,真空無名,無名名之父,無色色之母。為萬物之根源,作天地之太祖」(註8),就是借老子「道可道,非常道,名可名,非常名。無名天地之始,有名萬物之母」的「無」,正面詮釋涅槃意義。當然,僧肇也有依般若性空來解涅槃,上述以「無」代「空」之說,正反映了般若的反面思維(遮詮、對破)與中國人的正面思維(表述,界定)的距離。借道談佛,無疑是權宜之計,但在名相概念互相借代時,不免產生誤解,甚至對象化;然而,又潛伏了融匯貫通,發展新思想的契機。
二祖慧可與僧肇、慧遠一樣,入佛前「博涉詩書,尤精玄理」(註9)。他流傳的一則偈頌,首兩句云:「說此真法皆如實,與真幽理竟不殊。」可見他雖秉《楞伽經》為宗,卻浸入了道家(真幽)元素,故《續高僧傳》說他「專附玄理」。話雖如此,他對「自覺」卻另有創見。偈頌續云:「本迷摩尼謂瓦礫,豁然自覺是真珠。無明智慧等無異,當知萬法即皆如。愍此二見之徒輩,申詞措筆作斯書。觀身與佛不差別,何須更覓彼無余。」(註10)相對於達摩的「安心」法門,慧可把佛法統一於心,所謂悟,就是觀清淨之心,(自覺)無明不異於智慧。「這實際上也就把所觀之境由外搬到了內,清淨之心即是所觀的對象。」(註11)此說的確擴大了心的範圍,心的本質就是「清淨」,對貫通般若和佛性,邁出一步。(後來神秀所依的,就是這觀點,亦構成與慧能的思想分別,稍後再作說明。)
禪宗三傳至僧璨,把慧可的「心性說」發展成「即心即佛」,再配合般若中觀的「不二法門」和老莊哲學,是禪宗中國化的重要轉折。他的《信心銘》棄梵文術語,採本土語言,爽脆明快,直指心要。劈頭四句就清楚扼要指出:「至道無難,唯嫌揀擇。但莫憎愛,洞然明白。」(註12)「至道」是道家語,這裡指「佛性」的「真如法界」,本來不難達到,而最大的絆腳石,就是起了揀擇之心(分別心),以致「毫釐有差,天地懸隔」。「欲得現前,莫存順逆。違順相爭,是為心病。不識玄旨,徒勞念靜。圓同太虛,無欠無餘」「放之自然,體無去住。任性合道,逍遙絕惱。」(註13)同樣地,「玄旨」、「太虛」也充滿老莊玄學思想,特別是後面四句,明顯地以一種「任性、自然」的狀態,作為實踐方法,此除了承繼達摩不執文字的多元教法精神外,還開闢了從「日常生活」(坐禪以外,耕作、粗活等)悟道的可能性。銘又云:「真如法界,無他無自,要急相應,唯言不二。不二皆同,無不包容。」(註14)說明僧璨以般若「不二法門」為「真如法界」(佛性)的本質,所異於慧可,就是「真如」是不可求的,只能「現前」(親身體會),不在心外,亦不在內,佛性即心性,而悟道,無非是「一心不生,萬法無咎」(註15)而已。
轉佛性為般若 直指人心
「即心即佛」已然淡化了只本於《楞伽經》的如來藏色彩,道信和弘忍則進一步採用空宗經典傳法,成為禪宗依佛性為中心轉以般若為中心的分水嶺。道信雖然提到「我此法要,依《楞伽經》諸佛心第一」(註16),說法時,卻歸於空宗。他的《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》引《文殊說般若經》,指出「法界一相,系緣法界,是名一行三昧。若善男子善女人,欲入一行三昧,當先聞般若波羅密。如說修學,然後能入一行三昧。如法界緣不退、不壞、不思議、無礙、無相」(註17),就是以般若空觀說「法界一相」(佛性)。於修行時,則教「善男子善女人,欲入一行三昧,應處空閑,舍諸亂意,不取相貌,系心一佛,尊稱名字,隨佛方所,端正身向,能于一佛,念念相續」(註18)。這裡的「念」,雖是唸佛的形式,但佛性既是般若,「念念相續」,即念念般若。道信又引《大般若經》,進一步說「無所念者,是名念佛」。在「念」的意義上,他的觀點無疑與六祖「若得解脫,即是般若三昧。即是無念」(《壇經(宗寶本).般若品》)和「無者,無何事?念者,念何物?無者,無二相,無諸塵勞之心;念者,念真如本性」(《壇經(宗寶本).定慧品》)一脈相通。
五祖弘忍思想上繼道信「一行三昧」的般若佛性說,實踐上則兼承達摩「凝住壁觀」,立東山法門。他的《修心要論》(或《最上乘論》(註19),以「守心」為根本。字面上,「守心」跡近道家,而弘忍的「心」,其實是「涅槃之根本」,所守者,使「妄念不生,我所心滅,自然與佛平等不二」。這樣看來,「心」是「守」的對象,無論它是「真心」、「淨心」,都似乎回到慧可「觀心」的老路上。但弘忍弟子眾多,後更開出南北兩支,各有所本,而「守心」,儼然近神秀一系。印順在分析禪宗發展時,提出「從道信到弘忍而樹立起來的東山法門,大海一樣的兼收并蓄,決不是但以「守本真心」為法門的。應從《入道安心要方便》-「主體部份」到「雜錄部份」;《略統修道明心要法》到《修心要論》,更應從東山門下的不同禪門去理會出來」(註20)。可見弘忍法門的兼容性,同時亦顯示自弘忍以後,禪宗處於短暫的整理和歸納期,並由六祖慧能總其成。
傳法方面,弘忍的《最上乘論》廣泛引用《金剛經》、《十地經》、《維摩經》、《心王經》、《涅槃經》、《法華經》等,其論點多取般若空宗。據《壇經》記載,五祖以《金剛經》替慧能印心,可見其心要以破執為主。由是,禪宗以後以《金剛經》代《楞伽經》傳法,所本的就是般若空觀。其實,二祖慧可早已預言「此經(《楞伽經》)四世之後,變成名相,一何可悲」(註21),因為《楞伽經》所傳者為「藉教悟宗」的心法,只能從體驗意會,反之,愈加詮釋、疏解,便愈易生執著,慧可以後,諸楞伽師因意見不同,善禪師、豐禪師先後撰各種《楞伽》疏解,形成分化。《壇經(宗寶本).般若品》云:「若欲入其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,須修般若行,持誦《金剛般若經》,即得見性」「若大乘人,若最上乘人,聞說《金剛經》,心開悟解。」六祖取《金剛經》,除了其為空宗精華,簡明扼要外,更免於門人把「佛性,清淨」對象化,所謂「淨無形相,卻立淨相,言是工夫。作此見者,障自本性,卻被淨縛。」(《壇經(宗寶本).坐禪品》)
在修行上,弘忍則發揮「集禪不單在坐禪」的精神,不拘形式,四儀(行住坐臥)皆是道場,三業(身口意)皆為佛事,直接影響六祖「心平何勞持戒?行直何用修禪?」(《壇經(宗寶本).坐禪品》)的態度,故他反對形式化的「枯坐」,或者修「不倒單」,斥其為「是病非禪。長坐拘身」「生來坐不臥,死去臥不坐,一具臭骨頭,何為立功課?」(《壇經(宗寶本).頓漸品》)
本無菩提 何來塵埃
禪宗歷五祖,傳至東山法門,理論和實踐相繼完成以般若思想與生活禪為主軸的轉移,所待者,就是把戒定慧、般若和佛性徹底融匯貫通的時機。不少論者認為,六祖以後,禪宗方稱為「宗」,慧能亦成為開出「具中國特色的佛教」之重要起點。弘忍雖然弟子眾多,從慧能與神秀對「悟道」的不同觀點,就顯示出慧能確能契合心要,後弘法於南方,而神秀則在北方傳法,就成為以後南北禪宗的局面。
《壇經(宗寶本).行由品》記載了家傳戶曉的兩首偈。神秀偈云:「身是菩提樹,心如明鏡臺。時時勤拂拭,勿使惹塵埃。」明顯地,神秀所指的身、心,是菩提樹(佛性),其特點是「清淨」如「明鏡臺」,為了避免蒙塵,便當時加「拂拭」,換言之,「心」是拂拭的對象,是要「守」的東西(此說近於《修心要論》,亦與慧可「觀清淨之心」相似),心就變成實體(名相),仍有所執。所以五祖說他「未見本性,只到門外,未入門內」,如果要覓「無上菩提,須得言下識自本心,見自本性,不生不滅。」慧能遂回以一偈,云:「菩提本無樹,明鏡亦非臺。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塵埃?」句句針對神秀迷於「心」的「實性」,以「本無」、「亦非」進行對破。本來就沒有「心」,心既不生,亦是不滅,一顆「清淨心」(菩提樹、明鏡臺),無非源自神秀對心的執著。亦可以說,慧能並沒有說什麼(像《金剛經》「如來無所說」般),只是一語道破神秀把本性對象化,「自惹塵埃」而已。
但是根據《壇經(宗寶本)》為早的(敦煌本),慧能偈有另外兩個版本,其一云:「菩提本無樹,明鏡亦無臺。佛性常清淨,何處有塵埃。」其二云:「心是菩提樹,身為明鏡臺。明鏡本清淨,何處染塵埃。」我在這兒把三個版本並列,目的不在考證,只是藉此反映六祖開出的南禪,其實正一步步強調般若精神。因為縱使如敦煌本所載,慧能也指出「佛性」、「明鏡」本來就是清淨,就是不生不滅,亦無需刻意去觀、去守、去拂拭。此與「如來藏」思想把「佛性」視為實體大不相同。我同意洪修平在《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》的觀點,「在般若學的思想體系中,「清淨」、「本淨」等等名字與佛性——如來藏系的「心性本淨」之清淨涵義是有所不同的,它們實際上具有「性空」、「畢竟空」等意思」(註22)。加上當時慧能還未悟《金剛經》「應無所住,而生其心」而見性(《壇經(宗寶本).行由品》),這也許是夜訪弘忍前的看法。而宗寶本把慧能偈的第三句改為「本來無一物」,可能出於慧能,亦可能為南禪弟子所作,但無論如何,均說明破執精神越發展,越明顯,因為不管把什麼說成「清淨」(自性本清淨、佛性本清淨、菩提本清淨、還是涅槃本清淨),都構成對「究竟清淨」的執著,反之,無論把什麼說成「無一物」(自性無一物、佛性無一物、菩提無一物、還是涅槃無一物),又容易墮入「空見」。所以說「本來無一物」,實行抓無可抓,一破到底,因為凡有任何概念,都是迷人自築的執著而已,亦唯有此說方可充份體會佛陀的破執本懷。
除了在破執的體驗上,神秀和慧能層次不同外,從學理上分析,他們對五祖「一行三昧」的禪法,亦因前者立於「有」,後者立於「空」而各走各路。「神秀以真如、真心解「一行」,慧能以實相、自心解「一行」,空有的思想傾向各不相同,但他們都是立足於真空妙有契合無間、真心人心本來不二的立場,遵循著「行依佛行,心契佛心,返本還源,斷除凡習「的禪修途徑予以發揮的。事實上,北宗重觀心,南宗重隨緣」(註23),但亦由於神秀著意「觀心」,反易為「心」所縛,而慧能的「隨緣」,乃是一種自然的實踐方法,長於吸納,兼收併蓄,融匯貫通。
六祖屬於天才形人物,他目不識丁,出家前,以檢柴糊口,投東山門下後,還在幹踏碓的粗活,但從他的偈看來,對破執精神已然心領神會。可見他見道全憑直覺體驗,不在分析經教,每每能舉一反三,意會文字背後的核心思想,去蕪存菁地把意趣納入經驗層面,融匯貫通(就如陸象山「學茍知本,六經皆我註腳」一樣),再以自己的語言教示弟子。基於六祖隨緣施教的原則和學理上的局限,其說法特色並非透過如三論宗般,以細膩的思辯,重重對破,拆解問題,卻以簡單的表詮、通俗的語言、直接提示,完全適合中國,尤其是南方人明快活潑的思維模式。
綜觀《壇經》,雖然以見性為目標,但仍以破執精神為核心,有論者稱六祖南禪為「佛心宗」,我看不如尊為「般若佛心宗」,以其從般若解佛悟心,更加貼切。
六祖法門 無念為宗
六祖著重實踐,而《壇經》就開示了如何從般若(無念、無相、無住)體會(悟)佛性(自性)的法門。像大部份佛經把重點放在前面一樣,依《壇經》的品目編排來看,「般若品第二」和「定慧品第四」是其核心部份。六祖先解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」,勸大家持誦《金剛經》,指出「不悟,即佛是眾生;一念悟時,眾生是佛。」(註24)悟什麼?六祖引《菩薩戒經》云:「『我本元自性清淨。』若識自心見性,頓成佛道。」又說「但於自心常起正見,煩惱塵勞常不能染,即是見性。」(註25)是眾生,是佛,就在於悟與不悟,而悟與不悟,又在一念之間,一念「若起正真般若觀照,一殺(剎)那間,妄念俱滅。若識自性,一悟即至佛地。」(註26)此為六祖的「頓教法門」。
中國佛教對修行屬頓屬漸的爭論由來已久,為免弟子誤解法有頓漸而起分別,六祖在「定慧品」中,解釋禪宗修行的核心,「從上以來」(承自禪宗諸祖)都在「無念為宗,無相為體,無住為本。」「無相者,於相而離相;無念者,於念而無念;無住者,人之本性。」「念念之中,不思前境。若前念,今念,後念,念念相續不斷,名為繫縛。於諸法上念念不住,即無縛也。此是以無住為本。」「外離一切相,名為無相。能離於相,即法體清淨。此是以無相為體。」「於諸境上心不染,曰無念。於自念上常離諸境,不於境上生心。」(註27)
六祖施教從實踐入路,察覺到「無往」為人之本性,即是人本身就是處於不斷動念的狀態(依印度傳統,一呼一吸為一念,一念有八萬四千煩惱,意謂無盡煩惱),但如果隨著自己的執見,思前想後而起妄念,便會作繭自縛。他舉一個通俗的例子:「於世間善惡好醜,乃至冤之與親,言語觸刺欺爭之時,並將為空,不思酬(仇)害。」(註28)(慧能得法後常處險境,可能是他的現身說法),指出沒有想到報復,並非如仁者般以德報怨(《壇經》云:「若真修道人,不見世間過。若見他人非,自非卻是左;他非我不非,我非自有過」(註29)),而是一種無分別心(空)。不思前(前念)、不執於當下(今念)、不想後(後念)、不為自己的際遇和立場所帶引,就是「不住」。而且不單在生活層面,推而廣之,「於諸法(空有,生滅等概念)上念念不住」,才是真正的「無縛」。「無住」這不停滯兼自然而然的狀態,是緊扣著「無相」和「無念」的。因為「無相」是「外離一切相」,其實就是「不住於相」,而更重要的,是「無二相」,亦即以般若觀照,不墮二邊的中道,由是,則「無諸塵勞之心」(註30),乃至「法體清淨。此是以無相為體。」(註31)但有些佛弟子卻落入「常見、空見」,以為「佛境常住、諸法皆空」,所以六祖強調「無念」,要「於諸境上心不染」,所謂諸境,除了對世俗的貪瞋痴「不於境上生心」外,尤要破其對「空」(真如佛境)的執著,「若只百物不思,念盡除卻,一念絕即死,別處受生,是為大錯。學道者思之。若不識法意,自錯猶可,更誤他人。自迷不見,又謗佛經,所以立無念為宗。」(註32)要言之,「無住」、「無相」、「無念」三為一體,可以理解為「念念無住,念念無相,而不住於無相」。而「無相、無念」更起著體用的關係。「無者,無二相,無諸塵勞之心;念者,念真如本性。真如(無相)即是念之體,念即是真如(無相)之用。」(註33)
「三無」之中,六祖特別強調「無念」,因為他是從融攝般若和佛性入路,所謂「自性本無一法可得」(註34),與《金剛經》「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不謀而合。眾生解脫的關鍵,就在通過「無念行」來「識本心」。「若識本心,即本解脫。若得解脫,即是般若三昧,即是無念。何名無念?若見一切法,心不染著,是為無念。用即遍一切處,亦不著一切處。但淨本心,使六識出六門,於六塵中無染無雜、來去自由,通用無滯,即是般若三昧、自在解脫,名無念行。」(註35)這裡說明「無念行」是一種實踐方法。《壇經》常常提到「行直」,「欲得見真道,行直即是道」(註37)、「念念見性,常行平直,到如彈指,便睹彌陀」(註38)、「心平何勞持戒?行直何用修禪?」(註39)、「一行三昧者,於一切處,行住坐臥,常行一直心是也。《淨名經》云:『直心是道場,直心是淨土。』莫心行諂曲,口但說直;口說一行三昧,不行直心。但行直心,於一切法,勿有執著。」(註40)可見「行直心」者,不在咀邊,卻是在日常生活中,自然而然,時刻不執著於一切法。「無念」要「行」、「直心」也要「行」,「行」者,就是通向「頓悟」的持續過程。
六祖提倡「頓悟」,卻又說「本來正教,無有頓漸」(註41),其實並無矛盾。從法的完滿無礙而言,是一非二,所以法不只無頓漸,亦無空有諸相。但從修行而言,因「人性自有利純。迷人漸修,悟人頓契。自識本心,自見本性,即無差別。所以立頓漸之假名」(註42)。假名者,即因應眾生根器而施的臨時教法。雖然頓修漸修的目的都在見性,六祖採前者,為了渡「最上乘人」,強調「念念不住」、「念念無相」,就是時時刻刻都有悟道的可能性,要弟子們常處「無念」的狀態,一剎那間,熄諸妄念,即達佛地。此說與其他宗派由凡夫的「資糧位」、經十住十行十迴向到「加行位」、「通達位」、往「修習位」、經初地到十地菩薩、再至究竟佛地的層級階位說不同(階級昇進說本於印度精密的思辯方式和種姓制度傳統)。因為禪宗見道在「識自性、本性」,見性成佛,所謂「菩提只向心覓,何勞向外求玄?」(註43)六祖既把佛性從外境收回自心,常行直心、念念無念、當機立斷(妄念),就成為(頓見自性)成佛的必要條件。這觀點與主張漸修或先漸後頓,逐步放下執著者不同,因為它們均側重學理,分別修持戒定慧三學,著於境界高低,卻非通過體驗,融匯貫通。悟者,當下即空,若有絲毫執著,反覆不前,則仍未見性,故立「念念不住」的「無念」為宗,也成為以後南禪的大方向。同時亦可避免弟子們不把握現在,只尚功德,迷於「念佛求生西方」(註44),不思進取,但求來生再修的惰性。總的來說,六祖的「無念行」和「行直心」,是緊扣著他的頓悟法門而展開的,背後是求道的迫切性和當下見性的即時性,可以說是一種自由無滯的動態實踐。
自性戒定慧 行禪非坐禪
實踐既呈動態,說法自然靈活。六祖融般若與佛性為一體,在見性的大原則下,所有佛教基本概念都相通無礙。從根本的戒定慧三學來看,《壇經》云:「我此法門,以定慧為本。大眾勿迷言定慧別。定慧一體,不是二。定是慧體,慧是定用;即慧之時定在慧,即定之時慧在定。若識此義,即是定慧等學」。(註45)一改「由戒入定,由定發慧」的傳統,「莫言先定發慧,先慧發定各別」(註46),把定慧等量齊觀。持戒方面,六祖從來不尚條條框框的戒律,所謂「心平何勞持戒」(註47),只要常行直心、念念見性,行住坐臥均是功課,生活不離自性覺。若執於戒律規條,等如執於唸誦經文一樣,只會構成對象,反而有礙悟道。《壇經(宗寶本).懺悔品》雖然記載六祖為初學者依次說「五分法身香」,但仍統攝於自心見性的大原則下,從戒定慧到解脫,趣向「無所攀緣善惡」、不「沈空守寂」、「和光接物,無我無人」的「解脫知見」。此外,在《壇經(宗寶本).頓漸品》,六祖針對神秀北宗「諸惡莫作名為戒,諸善奉行名為慧,自淨其意名為定」的觀點,提出「心地無非自性戒,心地無痴自性慧,心地無亂自性定」,超越北宗把三學視為原則(實體)的看法,從般若破而不立入手,「若悟自性,亦不立菩提涅槃,亦不立解脫知見」,所以「見性之人,立亦得,不立亦得。來去自由,無滯無礙」,「遊戲三昧」之間。除戒定慧外,對一般佛教徒非常重視的功德,六祖在《壇經(宗寶本).疑問品》中標示福德和功德的分野,提醒弟子們「功德在法身中,不在修福」,「不是布施、供養之所求也」。再靈活地把「無念」、「離念」、「無染」等見性法門,代入修功立德之中,「見性是功,平等是德」、「內心謙下是功,外行於禮是德」、「自性建立萬法是功,心體離念是德」、「不離自性是功,應用無染是德」、「念念無間是功,心行平直是德」、「自修性是功,自修身是德」,重申法不在外境、不在事功,捨「無念」、「無相」、「無往」見性以外,別無他途。可謂進一步發揮《金剛經》:「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」的福德不及受持此經「乃至四句偈( 凡所有相,皆是虛妄,若見諸相非相,則見如來 )」為多,修福德遠遠不如觀般若的精神。
在靈活開示的大前提下,《壇經》的其他品目,處處洋溢六祖破執的法味,除著名的「心迷法華轉,心悟轉法華」(註48)、「我不會佛法」(註49)之外;以「惠(慧)能沒伎(技)倆,不斷百思想;對境心常起,菩提作麼長。」破「臥輪有伎(技)倆,能斷百思想;對境心不起,菩提日日長。」(註50)、以「無常者,即佛性也,有常者,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。」破「佛性是常……善惡之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。」(註51)、以「煩惱即是菩提,無二無別」破「以智慧照破煩惱」(註52)等,均從自識本性為宗,以般若觀照,「應用隨作,應語隨答」(註53),發揮禪宗不拘文字和概念的本色,依各人理解能力,隨類破其執見,使「邪來正度,迷來悟度,愚來智度,惡來善度」。(註54)
具體修行方面,六祖既以自性統攝戒定慧三學,對偏重「四禪八定」一類脫離日常生活的坐禪,特別提出意見。《壇經(宗寶本).宣詔品》云:「道由心悟,豈在坐也?」主要針對他們長住定境,斷念絕思的靜態修行,誤以為截斷與現實生活的聯繫,便可斷煩去惱,這想法恰恰就是走向「念念不住」、「念念無相」的反面。六祖的「見性」是流通的動態實踐,非停滯的靜態思維,故此「見境」、「見空」都是禪修的大忌。但是自從「安般守意禪」以來,僧侶崇尚小乘定境者不計其數,所以六祖一再斥責偏「止」而輕「觀」的呆坐,分別指出他們「執一行三昧,直言常坐不動,妄不起心,即是一行三昧。作此解者,即同無情(石頭一般),卻是障道因緣」(註55)、「又有人教坐,看心觀靜,不動不起,從此置功。迷人不會,便執成顛(顛倒)」(註56)。那麼,禪宗的禪,又是什麼一回事呢?《壇經(宗寶本).坐禪品》云:「此門坐禪,元不著心,亦不著淨,亦不是不動」(註57),既非「不動」,則處於動態,從動中觀,念念無間,念念無住,因為「心」原本就是在不斷變化,知此,則無所著,如果一味「觀空」、「觀淨」,無疑「起心著淨,卻生淨妄」(註58),反而被「淨」所縛。五祖融禪於生活,行住坐臥即禪的態度,結跏趺坐與否,已不重要。六祖更進一步,把般若思想與禪互相緊扣,融「無相、無住」入禪,「外於一切善惡境界,心念不起名為坐,內見自性不動為禪」,「外離相即禪,內不亂即定,外禪內定,是為禪定」(註59),所謂禪定,仍然回到「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」(註60),與時刻實踐「於念上離念,於相而離相,念念無間、念念無住」一樣。
習禪先通般若 自性四宏誓願
綜觀整部《壇經》,除了從「無念」、「無相」、「無住」見自性這中心思想外,六祖還對懺侮、歸依三寶、一佛乘、三身四智、三乘法、最上乘法、不生不滅、藏識、轉識等名相一一重新檢視,教示弟子。雖然品目次序未及空宗和唯識經典般編排嚴密,推論精細,卻勝在行文淺白流暢,長於對破,而且思想首尾一貫,始於般若品,終於三十六對法(註61),依「中道」義隨機開示。《壇經》核心不外念念無住,外離二邊,內見自性,與教外別傳,不立文字相應。禪宗歷五祖至慧能,終於完全融攝般若和佛性,消化本土儒道思想,融匯成以悟心為主的動態實踐法門,兼具中國文化特色的宗教,發展成以後南禪五宗的局面,而六祖則同為五家之祖。由融攝到開枝散葉,慧能無疑是禪宗得以大盛的關鍵。
然而像六祖這種天才人物畢竟萬中無一,他開出的動態實踐法門,僅為修行的大方向,見道則全憑個人體驗,但基於人們先天認知模式的局限,總要掌握一些道理,方感安全,能自由無礙地承繼心要者,少之又少,而且門人往往執於不立文字,忽略經教,根基淺者,對禪法多一知半解。流於表面、以偏蓋全,是歷來佛教發展遇到的死結。以印度佛教為例,原始佛教本來是最率真,以正見為先,至為簡單入世的,後學卻鑽進邏輯思辯,以法為觀察的對象,執於我空法有,滯於戒律經論,遂有龍樹菩薩的大乘改革運動,開出空宗;六祖不尚經教,不拘文字,以實踐破執見性為心要,開出禪宗,可稱繼大乘運動後,結合中印文化回歸佛陀本懷的另一次改革。大宗師如龍樹、慧能乃上上智人,於理於法自然通達無礙,惟後繼者利鈍有別,龍樹倡「空」,偶有執「空見」者,則誤解成「惡取空」,故他立《中論》,免弟子執空謗法;六祖不立文字、遊戲三昧,末流者執之,每每矯枉過正,謗經謗佛,淪為「狂禪」。
禪宗以心印心,由初祖至五祖,均密付心要予利根傳人,六祖遵五祖囑付,棄傳衣法後,習禪者日多,量大自然質降,雖有永嘉玄覺、青原行思、南嶽懷讓、馬祖道一等上根者領宗得意,後學卻捧著前人得法經驗,輯成大量語錄、公案、禪詩等,文辭不可謂不少。六祖故然並不排斥經典,《壇經(宗寶本).付囑品》云:「執空之人有謗經,直言不用文字。既云不用文字,人亦不合語言,只此語言,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直道不立文字,即此『不立』兩字,亦是文字。見人所說,便即謗他言著文字。自迷猶可,又謗佛經。不要謗經,罪障無數」;但亦提醒弟子「若不自修,唯記吾言,亦無有益」(註62),不希望他們變成「知解宗徒」(咬文嚼字者)。六祖弘法數十年,見道者尚且不多,禪風於唐宋大盛後,看語錄的,悟道者少,滯文者多;辯公案的,談禪者多,見性者少,禪門既廣,以至有貪慕名聞利養之徒,呈口舌之快,「口頭禪」成風,故弄玄虛,混淆後學。印順指出:「禪宗,自有他的偉大處。但他偏重心性的體證,過著山邊林下的淡泊生活,有著急了生死的精神,雖自稱為教外別傳的最上乘,而作風卻活像聲聞行徑」(懷抱上,慈悲不足);「深邃的義學,精密的論理,都被看作文字戲論而忘卻了,這是佛教中偏重智證的一流」(註63),(以至)「有些空談心性,(正如)儒者不重視六經,(若果)學佛不究三藏,自以為直探本源,而不知容易流於邪僻」(註64)(教理上,粗糙淺薄)。
自南宋以後,禪宗已從高峰滑落,並逐步為理學所攝。印順說:「(儒者)在『易』,『大學』,『中庸』,『孟子』的思想基礎上,融攝了道學與佛學,特別是佛教的禪宗,發展為體系嚴密,內容充實的理學」(註65)。當代禪學復興,但若缺乏篤實的佛學基礎,光從公案語錄入手,好辯者往往以為禪乃文字遊戲,嚴肅者又責其不合邏輯,語無倫次。近年來,歐美也不乏習禪人士,一位西方學者愛倫維特( Alan Watts )說:「在某些西方人圈子裡所流行的禪只是適合於精神上的混亂而已。它表現了他們對習俗,倫理,和宗教的一種不可理解的不滿。它象徵了他們在機械所窒息的世界中要恢復自性的迫切需要。但是由於只恢復意識經驗,使西方的禪學帶有道德放任的色彩,而忽略了中國和日本禪宗那種嚴格的訓練和嚴肅的傳統。」(註66)
可見禪宗易說難行,若非從破執精神入手,只談談禪、鬥鬥機鋒、打打坐,與放逸何異?六祖說過「法無四乘,人心自有等差。見聞轉誦是小乘,悟法解義是中乘,依法修行是大乘。萬法盡通,萬法俱備,一切不染,離諸法相,一無所得,名最上乘。」(註67)「最上乘人」可以離經教自修自證,我輩(大、中、小乘人)欲習禪宗,還是循原始佛教《阿含經》入路,再習般若空宗經典,不妨依六祖提議的《金剛經》、《淨名經》(《維摩經》),此外還有《小品般若經》、《心經》、《妙法蓮華經》,繼而習《華嚴經》、《涅槃經》等為基礎。明白諸法皆是「假名施設」,本無大小二乘、空有二宗、漸頓法門、通教圓教之別。再讀《壇經》、公案、語錄時,方容易體會禪師們的意趣而不失其宗。
禪者語默,論亦僅止於此,言之不足,發願實踐可也。且借《壇經(宗寶本).懺悔品》中四宏誓願,改編為「自性般若四宏願」作結,與各位同沐法雨。
自心眾生無量誓願度,實無眾生可度。
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,實無煩惱可斷。
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,實無法門可學。
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,實無佛道可成。
附註
1 .《禪宗語言》 周裕鍇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12月初版 11頁
2 .《中國佛學思想概論》 呂澂著 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5年10月初版 127頁
3,4 .《大正藏》 第16卷 499頁
5 .《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》 洪修平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年1月初版80-81頁
6 .《中國禪宗史》 印順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9月第二版 序 7頁
7 .《高僧傳》 中華書局 1992年 249頁
8 .《大正藏》 第45卷 143頁
9 .《大正藏》 第51卷 220頁
10.《續高僧傳.僧可傳》 第19卷
11.《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》 洪修平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年1月初版 88-89頁
12 - 15.《景德傳燈錄.第30卷》 《大正藏》 第51卷 457頁
16 - 18.《楞伽師資記》 《大正藏》
19.《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》 洪修平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年1月初版 122-123頁 傳《修心要論》即是《最上乘論》,為弘忍門人所作,尚待考證。
20.《中國禪宗史》 印順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9月第二版 64頁
21.《五燈會元.僧可傳》 第16卷
22.《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》 洪修平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年1月初版257頁
23.《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》 洪修平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年1月初版 145頁
24 - 26.《壇經(宗寶本).般若品》
27 - 28.《壇經(宗寶本).定慧品》
29.《壇經(宗寶本).般若品》 「無相頌」
30 - 34.《壇經(宗寶本).定慧品》
35.《壇經(宗寶本).般若品》
36.《景德傳燈錄.第30卷》 《大正藏》 第51卷 457頁
37.《壇經(宗寶本).般若品》 「無相頌」
38.《壇經(宗寶本).疑問品》
39.《壇經(宗寶本).般若品》 「無相頌」
40 - 42.《壇經(宗寶本).定慧品》
43.《壇經(宗寶本).疑問品》 「無相頌」
44.《壇經(宗寶本).疑問品》
45 - 46.《壇經(宗寶本).定慧品》
47.《壇經(宗寶本).疑問品》 「無相頌」
48 - 50.《壇經(宗寶本).機緣品》
51.《壇經(宗寶本).頓漸品》
52.《壇經(宗寶本).宣詔品》
53.《壇經(宗寶本).頓漸品》
54.《壇經(宗寶本).懺悔品》
55 - 60.《壇經(宗寶本).定慧品》
61.《壇經(宗寶本).付囑品》
62.《壇經(宗寶本).般若品》
63.《妙雲集.下編之六.我之宗教觀》 印順著 正聞出版社 1990年5月12版 40頁
64.《妙雲集.下編之六.我之宗教觀》 印順著 正聞出版社 1990年5月12版 41頁
65.《妙雲集.下編之六.我之宗教觀》 印順著 正聞出版社 1990年5月12版 69頁
66.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 吳經熊著 吳怡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1995年6月初版第18次印刷 10頁
67.《壇經(宗寶本).機緣品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