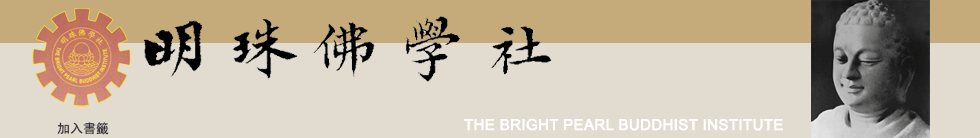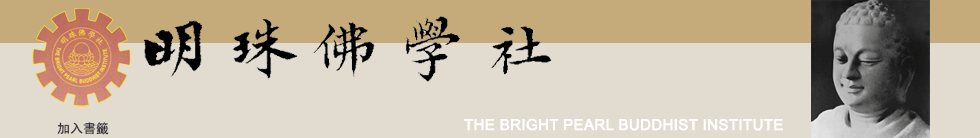一、前言
釋尊一生說法四十五年,教示弟子以「知苦、斷集、證滅、修道」的四聖諦,令無數弟子得以消除生命中的憂悲惱苦,證入徹底解脫之涅槃境界。在他以八十歲那年入滅之後,佛教隨著弟子們的受持、傳承、弘化,在印度各地弘揚。在佛滅一百年後,更得到阿育王的信仰及大力推動,令佛法迅速地分佈於印度以至其它地區去。
由於佛弟子們恪守著佛陀臨終時的「以法為師」的教示,於是對佛陀的法語展開研究,從而產生了不少的阿毗達磨論典。隨著各地遊化的弟子在生活習慣及對佛法理解上的差異,終於令致百餘年後出現教派分裂,佛教出現了為期約五百年的「部派佛教時期」,產生了為數約二十個的部派。這期間大量阿毗達磨論典湧現,使法義之間愈趨複雜。
在民間,在家佛弟子對佛陀的懷念與追思,透過向佛塔、佛舍利、遺物、遺跡的禮拜,以求身心得以慰藉,由此而發展了對佛陀的信仰;另一方面,佛弟子亦從追思及撰述佛陀的生平,進至追溯其前生的求道生涯,逐漸形成了佛傳文學。再加上部份佛弟子有感於傳統部派論師對法義的執著,於是對佛陀的解脫精神予以反省演繹,並號召佛弟子們重新以佛陀為學習對象。乃至因緣成熟,在佛滅後約五百年左右,大乘思想匯合成流,在印度東部逐漸開展出來。
大乘佛教首先是般若經的集出,針對部派弟子的法義予以掃蕩,以符合佛陀的解脫精神,與此同時,菩薩乘的觀念亦逐漸形成,直接顯示求道者的心懷與毅力。初期大乘佛教思想依著般若經而逐漸開出幾個重要的法門:以淨土經典為主的信仰門、以華嚴經典為主的實踐門、以法華經為主的慈悲門,及以般若系經典為主的智慧門等等。
大乘經典陸續集出,從不同的途徑傳到中國,透過高僧大德們的翻譯,再經過了幾百年的消化與研究與分類,中國佛教由形成學派而致發展了不同的宗派,同時也對印度傳來的佛教經典教進行了整理與判別。
二、古代大德的判攝
由於部派系統和大乘系統的經典是隨著佛教的信仰同時傳入,中國人只從經典的內容上理解,缺乏歷史背景的認識,因此認為所有經典都是佛在世時親口所說,並依此來接受其中義理,作為信受基礎。
時間一久,傳來及翻譯的經典愈來愈多,內裡的義理或有不同、或有矛盾,引起了不少解釋上的困難和爭論。為了融通各經典之間的矛盾,顯示各各不相妨礙,於是判釋佛陀經教的活動產生,希望能夠全面肯定所有經典的價值與地位。判教即是將所有的佛典從形式上進行分類,從內容上組織整理,並評介其高下。判教的活動在魏晉時代已經開始進行,南北朝時代眾說紛紜,有從時間上來分判,有從教義的內容上來分判,有從教法來劃分。從判教的過程上,除了列出經典的分類外,更從中判別自宗認為是最究竟的說法,從此建立起自已所宗經典的最重要地位。歷代判別佛教系統而影響較大的,便是智者大師、玄奘大師、義淨大師及法藏大師等。
甲、智者大師之判別
天台宗智者大師的判教論說,是從三方面來對佛法進行了判別,即佛陀的說法時期、說法方式,及說法內容來作分判的,合稱為「五時八教」。其中的時期分類稱為「五時」,即「華嚴時、鹿苑時、方等時、般若時、法華涅槃時」;關於說法方式的分類稱為「化儀四教」,即「頓、漸、秘密、不定」四教;至於內容的分類,便是「化法四教」,亦即「藏、通、別、圓」四教:
(1) 藏教 ─ 藏教是指小乘部派的三藏教,亦即是原始阿含及部派經典。
(2) 通教 ─ 通教是指從部派到大乘的過渡之說法。如《般若經》、《大寶積經》、《維摩經》等。
(3) 別教 ─ 別教即大乘菩薩個別的教法。如《華嚴經》、部份《般若經》等。
(4) 圓教 ─ 圓乃大乘終極之義理,圓滿具足而又無礙,直顯佛陀之真實義。代表著圓教的經典有《法華經》和《涅槃經》等。
乙、玄奘大師及義淨大師的判別
唐朝初年玄奘大師前往印度留學十七年,遍遊印度各地,學習印度諸宗大師的學說,可說是會通大乘佛學的大師,在他回來後的記述中,印度大乘宗派當時只有中觀派及瑜伽派的存在,而且玄奘大師更著有《會宗論》來會通空有二宗的爭執,得到當時其師戒賢論師的讚賞。
較玄奘大師稍後的義淨大師,亦前往印度求法,入學於那爛陀寺十一載,其後撰寫有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,述說印度的見聞情況。他在卷一中云:
「所云大乘無過二種。一則中觀,二乃瑜伽。中觀則俗有真空,體虛如幻。瑜伽則外無內有,事皆唯識。」
由於玄奘大師與義淨大師均留學印度,親眼目睹印度佛教盛況,因此其言論自有一定的地位與份量。故傳統以來,很多學者皆認為印度大乘佛教就只有二個系統,即是中觀與唯識二派,簡稱為空、有二宗。後來,從西藏佛學的傳統經典《四部宗義》,亦支持此說,認為大乘即屬中觀與瑜伽二大系統。
丙、法藏大師的判別
不過,華嚴宗的集大成者法藏大師,對於印度傳來經典的統合看法,卻有所不同,在他的《大乘起信論義記》中,他別樹一幟的說道:
在這個判別之中,法藏大師第一次指出了大乘佛教有「如來藏緣起宗」這一宗別,他亦以此宗來建立他的華嚴宗真心系統。
丁、佛教界的爭議
在中國佛教學界,一向根據玄奘大師及義淨大師所見所聞所述,認為印度大乘佛教,不外是空有二大系統。他們覺得玄奘大師在印度十多年,完全沒有提到印度大乘有著第三系的思想及人物,如果有的話他一定會提及的。此外,義淨大師前往印度留學時,亦只見大乘中觀、瑜伽兩派。故此,不少學者是拒絕承認印度大乘有第個三系統的。
不過,在傳來中國的經典之中,有一部份大乘經典,的確是與空宗和有宗有著不同的思路,這些經典並非孤立的傳來,而且部份是極為著名的經典,如《勝鬘經》、《如來藏經》、《涅槃經》等,這類經典的內容及思想路線,與前述兩系均不大相同。
面對著如何處理這類經典的問題時,部份學者便以有宗的新譯、舊譯的不同處來會通,有些學者索性否認這些經典的真確性,直斥其為中國人偽造的經典,例如《楞嚴經》及《大乘起信論》等經論,便長期在中國佛教界引起真偽的爭議,直至民國初年仍未有停止。
三、近代大德的判攝
民國以來,以太虛大師與印順導師對佛教的判攝最為有名。太虛大師從教理上的判攝,他將大乘佛教判攝為三宗,按其發展先後,分別為:「法界圓覺宗、法性空慧宗、法相唯識宗」。他以傳統中國佛教的看法,將法界圓覺宗判為最高,代表著佛法最究竟之法義。
印順導師受到太虛大師的啟發,亦對印度佛教進行了系統的劃分。他在《印度之佛教》一書中,亦將大乘法義判為三系:「性空唯名論」、「虛妄唯識論」、「真常唯心論」,而以性空唯名論的緣起性空中道說為究竟之說。後來印順導師經過了與太虛大師及當時大德學者的往返論辯,使他的判別更見堅穩,並差不多成為了現時中國學人對印度大乘佛法系統判攝的定說。
四、現代學者的學習態度
經過了近世數十年來的討論與研究,以及印順導師等大德們的努力探究,性空學派、唯識學派與真常學派鼎足而立,共為印度佛教思想的三大系統,基本上已是證據確鑿,無容否認,因為文獻資料俱在,可說已經成為定論。
我們現時並非要評價個別系統,或是褒貶其中的學說,以繼續引起爭議。我們應該透過前人的研究成果,循著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脈絡,探討大乘三系思想的源流、經論、人物及流轉與影響。從比較三系思想路向的異同及特色,進而探討現代不同系統的學者們對佛教經論的演繹,使我們可以超越宗派的認知與盲從附和,客觀地探究三系思想在教化上的方便與價值。
從概略地認識大乘三系的論說,當有助我們從佛法中超越宗派知見,返本探源,了解佛陀的本懷,在浩瀚的佛法義理中知所抉擇,然後應用於自身的佛法實踐之中,真正踏上解脫之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