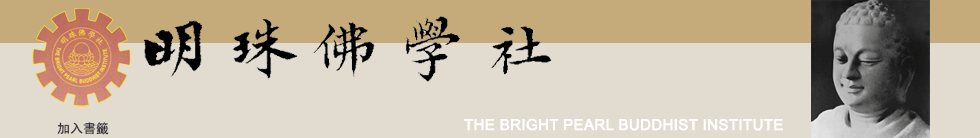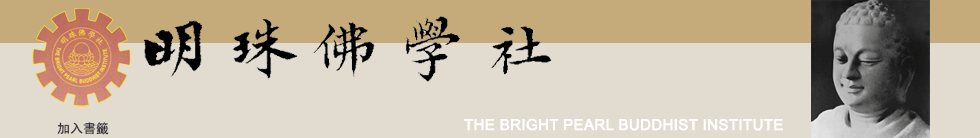中國人以「物我兩忘」之藝術境界為高,印度人以「梵我一如」為終極目的,西方人則以「我思故我在」為哲學的里程碑。究竟這個「我」是甚麼?如何去理解這個「我」呢?
當人類意識到生命的存在時,便潛意識地以為有一個生命的主體存在,這個主體稱之為「自我」,於是主客分立,區別開自我與外界,成為了兩個對立的範疇。人們有著「自我保護」及「自我延續」這些要求,期望「自我」永恆存在,但可惜的是,我們卻會因衰老、疾病而死亡而壞滅。現實所見的情景,與人們的期待是相違背的,於是引起心靈的不安,種種焦慮、不安、憂悲、困擾、苦痛隨之而來,惱亂著身心,不得自在。
「吾心似秋月,碧潭清皎潔,無物堪比倫,教我如何說?」 -- 《寒山詩》
大約在2600年前,印度的釋迦太子經過六年的苦修,終於在菩提樹下,解脫一切執見的束縛,成為了一代聖者。在他徹底醒覺後,他曾經一度猶豫,應否將他所證悟的道理,解釋給世人知悉?會不會徒勞無功?然後他看到面前的蓮池,在蓮池中,有不同的蓮花在生長著,有些蓮花是淹沒在水中,有此則已生長到水面,有些更透出水面,不為污水所沾染。於是他想到,同樣的,世間之中,也有各種不同根器的人,雖然有些人是愚昧的,也會有一些人是能了解他所體驗的,於是釋尊才決定說法。
佛陀從生命所面對的種種憂悲惱苦、疑惑恐懼作層層追溯,他看到世間無盡苦惱的根源,正是世人因無知而執著,以為有一個永恆不變、獨立存在的「自我」而來的。佛陀就是第一個徹底擺脫了這個「我執」的枷鎖,得到自由自在的聖人。
「色無常,無常即苦,苦即非我,非我亦非我所,如是觀者,名真實觀。」 -- 《雜阿含經》
佛陀為了啟發弟子,於是說出了「無我」的教說,教示弟子通過觀察身心的無常變化來放開對「自我」的執著。他指出,我們當觀察自己的身體時,便很容易覺察到它是不停息的變化,而這最後是歸於壞滅(苦)的。身體會壞滅的話,它便不能是一個永恆的「自我」了,它不是自我的話,更不會是由自我所擁有的東西。能夠這樣觀察的話,便是如實正確的觀察了。除了物質身體之外,其餘感受、思考、意志、認知等心理現象,都祇能看到不停的變化而已,其中何來有不變的「自我」呢?
「世人顛倒,依於二邊,若有若無,世人取諸境界,心便計著。……如來離於二邊,說於中道。」 -- 《雜阿含經》
由於人類的思維特性,往往將概念二分,以掌握其意義,成就知識。人們一方面建立主客的對立,另一方面再將自我與對象事物執著不放,或執其有,或執其無。因此,佛陀主要是要破除人們的執見,而並非是要討論對象是否存在的。他只是教示我們在實踐上放開對「自我」這個觀念的執取,並由此而達致心解脫。一般人不明就裡,便以為佛陀說「有」說「無」,實際上佛陀說「無常」,並非是真的說對象是無常,而只是要我們消除對「常」的執見;他提出「無我」的說法,亦是要破除弟子對「我」的執取,當「我」的執見放下後,「無我」亦應同時放開,這樣才能真正得到解脫。唯有對二邊思維概念皆不執取,方能如佛陀所說的處於中道,「中道」即是正向於解脫的方向。
「諸佛或說我,或說於無我,諸法實相中,無我無非我」 -- 《中論》
人們如何能身處於這個概念二分的語言思維空間之中,破除對二邊概念的執見,同時還處身於這個概念世間中呢?佛陀指出這便要通過對身心專注的訓練,使心念能了了分明於當下之一刻,由此而體察到我們的心念,無不是處於緣起激流之中。種種思維執見,只不過是一堆堆概念的延續,其中根本沒有永恆不變的成份,亦沒有獨立自存的性質,我們都是依著身心概念的變化,隨著時空的轉換而前進。其中何來有「有我」?何來有「無我」?生命只是緣起緣滅的觀念流轉而已。
「大聖說空法,為離諸見故,若復說有空,諸佛所不化」 -- 《中論》
針對於後來的佛弟子執著於「有我」、「無我」的討論時,大乘佛教便提出了「空」的論說,試圖從另一角度來破除人們對「有、無」二邊的執見。「空」的提出,並非從存有論的角度來討論事物的「有」或「沒有」,而只是指出我們不要執著有這個「不變自性」的觀念而已。佛家提出「空」這個說法,正是要破除弟子對一切事物的執見,因此說出「一切皆空」。但世間人永遠是存在著執見的,因此佛家在提出「空」的同時,亦舉出了「空亦復空」的說法,提醒我們千萬不能執實了這個「空」的見解,以為是真理,否則又會形定了另一層的執見了。
其實,修行只是不斷破執的過程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