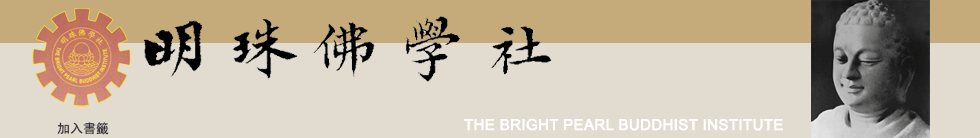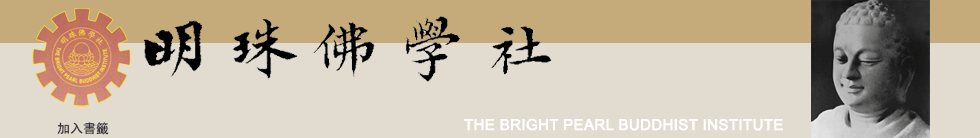驟眼看世間,事物不斷遷流變動,如流水落花、日出日落、月圓月缺、寒來暑往、生老病死等等。四季的交替,人事的變化,正標示著世間變幻不定。於是覺得世事遷流不息、無常變遷,這乃是人之常情。但在佛家看來,卻並非如此。在佛教很多的經典中,都針對著「世事無常,變動不居」的看法而進行了反思。
《維摩經》云:「諸法無所從來,去者無所至。」《放光般若經》說:「法無去來,無動轉者」。這都是說明事物是無所謂「來去」的流轉。何解呢?原來佛家認為一般人在自覺存在時,便已將自我與外界割裂,成為了內外主客的兩個界限,於是在思維過程中時,總是會以這二分的方式來瞭解世間事物,成就知識。這種二分的性格便形成了思維概念的特性,亦成為了自我執著之源。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,成就解脫,就是打破了思維概念的枷鎖,去除了這個約束,成為自由自在的聖者。
佛陀的本懷,原是為了破除人們的執見,解脫由執見所引生之煩惱。這些執取有從「自我」出發的,有從「觀念」出發的。佛家稱之為「我執」、「法執」。在佛教看來,執著破除便能成佛。因此古往今來,無數佛教大師,都是努力於找尋方法來破除我執與法執,然後致力於破除弟子的執見,如此而已。
如何破執呢?在大乘佛教般若系的經典中,發展出了一套針對學者執著而使用的方法,我們稱之為「對破」。上文說,一般人在思維過程上,習慣以相對的概念來認識事物,如長短、大小、前後、多少、高低、善惡、貧富、真偽、虛實、強弱、動靜等等。人們總是以這些二分的前題下,來認識事物,乃至對世間人事進行價值判斷,於是引起種種爭執苦惱。佛家便是利用這語言概念的二分特性,於是舉出執見的另一端,以動破靜、以主破客、以來破去、以大破小、以聖破凡、以無我破有我、以無限破有限,如此致使對方放下自己的執見。執著破除之當下,更不執取老師之言,便能成就覺悟,如此方能了悟所謂「言外之意」。例如佛家說「無常」,其旨意只是破除人們對「常」的執見,若放下對「常」的執見後,亦不應執著有「無常」的。因此佛家表面所說的「無常」,背後卻是要我們破除「常」與「無常」的執見,這才是佛家破執的精神。
禪宗六祖惠能便以這套方法來教示後人,《壇經》中最著名的偈頌:「菩提本無樹,明鏡亦非台,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塵埃?」很多人以為惠能這首偈頌是主張甚麼都沒有的「虛無主義」,其實是誤解了這首偈背後之意義,這首偈頌只是針對著神秀所寫的頌偈而破斥其執見而已。神秀所寫的偈頌云:「身如菩提樹,心如明鏡台,時時勤拂拭,莫使惹塵埃。」我們逐句對照惠能與神秀這兩首偈頌,便可看到其背後對破的精神了。後來惠能大師更針對當時臥輪禪師所說的偈頌而作出了破斥。我們對照這兩首偈頌,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對破方法的應用:
臥輪頌:「臥輪有伎倆,能斷百思想。對境心不起,菩提日日長。」
惠能頌:「惠能無伎倆,不斷百思想。對境心數起,菩提作麼長?」
由運用對破方式的發展,後來禪宗大師們突破了語言概念的局限,成就「法無定法」的教法,直接在日常生活上,用任何現成的教具來進行破執的教示,於是詩詞歌賦、書畫琴棋亦可,棒喝打罵、刀光劍影齊出,皆可以成為佛教大師們的教具。於是禪宗便由刻板的學堂而進入了生活上多元化的活動教學,將佛法融入了中國文化之藝術、音樂、繪畫、建築、文學、哲學各個領域之中。
對於動者與靜者、動與靜的見解,不外乎以下的四句說法。但無論「動者常動,靜者常靜」也好、「動者不常動、靜者不常靜」也好、「動者常動亦不常動、靜者常靜亦不常靜」也好、「動者非常動亦非不常動,靜者非常靜亦非不常靜」也好,其實何來動者?何來靜者?何來動?何來靜?這都是自我心靈的分別執取而已。從聖者的角度來看,根本就沒有「動」、「靜」,更何來「動者」、「靜者」呢!
《金剛經》云:「凡所有相,皆是虛妄」。說動說靜,都是癡人夢中說夢話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