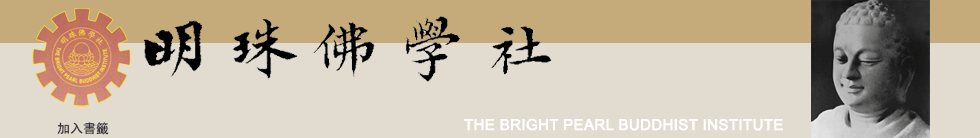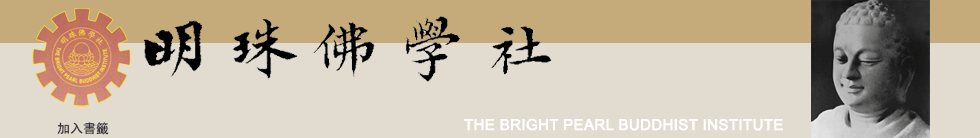誰與斯人識見同
—— 懷念本社創辦人明慧法師
一、不接受在家人頂禮
一九六八年,我有幸得遇明珠創辦人明慧法師,從此對佛法的理解,有了根本的改變。
那年夏天,我與好友正在梁隱盦先生的協助下,籌辦一所夜中學。一日,隱盦先生忽對我説,有一佛學社在夜間為社友開辦進修班,設有佛學、國文、英文、書法等課,正欠缺英文導師,問我可否為他們擔當這個義務,每周去上一次課。我信賴隱盦先生為人,所以一口便答應了。就這樣,我開始踏足明珠,認識了明慧法師,往後更成為明珠的常客,並蒙法師視我為忘年之交,情同莫逆,因緣真是奇妙的!
未遇明慧法師之前,我很少與出家人接觸。有時參加一些法師主持的講經法會,總覺他們威儀整肅,高不可攀,非我凡輩所得而親近。但第一次接觸明慧法師,感覺完全不同。他平易近人,謙沖有禮,臉上泛現慈和的笑容,沒有半點架子,也沒有使人覺得他是一位高出在家人一等的法師。我當時還以為他和我初次見面,不免客氣一點,但後來察覺,他那謙和有禮的態度始終如一,乃出於自然,不由造作,而且並非只對我如此,對日常接觸的人,都莫不一樣。
法師能夠這樣待人謙和,沒有貢高我慢,除與個人修為有關之外,原來還由於他有一種獨特的見地。他認為出家人如非真實修行,至於賢聖,則與凡夫無別;所異於俗人者,只是去除鬚髮,著偏領衣,穿多耳麻鞋,扮相不同而已。所以,出家人是否值得尊敬,全看所作所為能否如法,而與其扮相無關涉。基於這種見地,他不要非他弟子的在家人向他頂禮,因為他們只是向他的扮相禮拜吧了。可以想見,這種反傳統的思想和做法,教界中人會多麼難以接受。記得有一次,道慈佛社社長楊日霖居士忽然對我表示,已很久沒有見過明慧法師了,想去看望他。我便帶楊居士到明珠去見法師。楊居士向來對出家人執禮甚恭,一見法師,很自然便即彎身跪下頂禮,但法師亦立即彎身,以手阻截楊居士下跪,一邊説:不必頂禮,不必頂禮。雙方爭持了一陣子,終於楊居士還是沒有頂禮成功。從明珠出來,他忍不住對我説,出家人接受在家人頂禮是禮法如此,絕對應該。法師堅持不受禮,未免有點乖僻。很明顯,他對法師的做法是大不以為然的。此後,他就再沒有向我提及法師了。
楊居士的想法,相信一般佛教徒都可以理解,法師的見地,教界中人同情的恐怕就沒有幾個。但對我來説,法師的表現卻有助我消除對出家人的神祕感,使我敢於去接近出家人,並以持平的態度處之──如果是有道有守的,則敬之如菩薩;如果只是扮相不同,則視之如常人,再也不像以前那樣,只知一律敬畏。往後,本著這種平實的精神,我對佛教經典亦有所抉擇,辨知何者是世界悉檀,何者是第一義;何者是方便,何者是真實。所以,法師的言行,對我的影響是深遠的。
二 願能改革中國佛教
我到明珠教英文,始於六八年七、八月間,和法師晤談,大都在上課前或下課後,時間並不多。但法師對我似乎是一見如故,説話之中帶親切,眉宇之間見歡喜。由於他的親切,在他面前,我感到無拘無束,像對著一位熟稔的長輩,又像是對著一位老朋友,當時直覺和他很有緣份。九月,夜中學辦,有一晚,我正在夜中學辦公,法師的高徒容君智寶忽然送來一幅裝裱好的字,説是她的師父寫給我的。我細看那幅字,不禁心頭震動。字云:「海內尋知己,天涯才識君,傳薪多借重,從此挹清芬」。看後第一個感覺是,法師太言重了,他出家數十年,在教界為長老,善友與弟子眾多,我憑甚麼可作他的知己?而學佛時日尚淺,對佛法猶未深究,更何足以擔當傳薪重任?我一方面感激法師的知遇,一方面卻又有點納罕:為甚麼相識短短兩個月,法師便這樣對我厚愛?這個疑團直至他辭世後才得到打破。這留待下文再作交代。
社友進修班持續了幾個月,便因法師健康欠佳而停辦,但我仍不時到明珠,與法師晤談。他最常談到的,是中國寺院人事與制度上的種種弊陋。他指出寺院濫收徒眾,非為培養僧材,只用來充當各種庶務,以維持一寺的運作。為求經濟充裕,一般都著重簽香油,做功德,安靈位,設齋菜等生利事業,續佛慧命的事功,反成次要。所以,徒眾雖多,卻是真實僧少,啞羊僧眾。此外,佛法倡平等,但寺院中,上座、住持、班首、執事,與下面一般清眾、學人,彼此待遇,相差甚遠。他舉述不少事例,此處不及細説,簡括言之,是上面豐富,下面清苦。而清規封建苛嚴,不合情理,違背佛制,大家卻硬要遵守;原來如法的戒律,卻反為可有可無,不予重視。所謂「戒律可以通融,清規必須尊重」,本末倒置,莫此為甚。每談及此種種弊陋,他便神情激越,不住嘆息,強調非改革無以挽救中國佛教之衰。為此,他創辦明珠,一開始即規定:明珠一不得向外界募捐;二不得主動勸請外人入社;三不得做功德法事,以謀收入。明珠的成立,祇為舉辦佛學班,以弘揚正法,一切經費,須由社友合力維持。由此可見,法師是決心要改革佛教的。
三、倡弘性空中道之教
另外多談論的,是他在佛學思想上的見解。他早年已潛心內典,後於南京寶華山隆昌寺受戒學律,有機會遍閲清龍藏及日本大正藏,然後對佛教大小乘教義,有一全盤了解。另一方面,他又與駐錫星加坡的遠參法師通訊,請教法義,得遠參法師指導,始知佛教有權實真偽之別。從此,他就捨棄中國佛教宗派成見,專弘揚印度佛教之本義。他的思想雖得自遠參法師啟發,卻並非遠參法師的弟子,彼此對佛法的取捨亦不盡相同。遠參法師主要弘揚法華一乘,旁及大乘般若性空之理;他則倡導原始佛教之基本教義四諦十二因緣,由此下接大乘性空中道之教,而一一皆歸本於無常、無我、湼槃寂靜等三法印。他認為諸法本空,不以消滅為空。(此即維摩經所云:「色即是空,非色滅空,色性自空。」)這種理論,最為平實,亦最能說明一切現象的真相,無玄想不切實際之弊。佛教傳入中國後,發展為宗,混和印度婆羅門奧義書所説的梵,大乘後期所説的如來藏,與中土道家所説的道,建立真心、本性、佛性、本來面目等名異實同的本體論。這是有違佛教正理的。
我踏足明珠之前,已學佛多年,但從未聽過像法師那樣的説法,一向所學,都大抵不離中國佛教真常唯心之説,尤喜楞嚴一經,以為該經一如圓瑛法師所説:「闡明心性本體,為一代法門之精髓。」又哪裡知道,佛法中更有性空中道之教,為較如理。也許我舊習未深吧,向法師請益法義沒有太多次,我便不再執著以前所學,虛心接受他的慧解。不過。説真的,由於他所開示的法要確是聞所未聞,非常獨特,我於接受之餘,仍不免略帶疑惑:究竟這是否一條最正確的學佛之路?直至稍後,我研習印順導師的著作,發覺導師竟然也同樣不以中國佛教的真常論為第一義,並提示相同的學佛路向──由阿含的緣起,接於般若的畢竟空,以達至龍樹的中道。所不同的,法師剛猛強硬,不留餘地;導師則含蓄委婉,尚存方便。至此,我再無疑惑,決心修學中觀,並發願弘揚之。這時法師已辭世,我乃皈依導師座下。在悟解正法的歷程中,法師開導我於前,導師成就我於後,兩位思想上的巨人我都幸能親近,這真是有生以來最大的福報!
四、志願完成遽爾長逝
法師自從健康欠佳,停辦社友進修班後,一直在調養身體,不敢再開班,只於明珠舉行周年紀念的時候,為社友開示法語。至七二年春夏之間,法師忽然對我表示,明珠之創辦,純為弘揚正法,躭擱了這麼多時日,還不曽做到分毫,實在感到著急。他覺得不能再等了,所以,想在暑假過後,開辦佛學初階班,公開招收學員,希望我能幫助他,分擔講席。我以為法師祇是説出心中的希望吧了,不會立即便進行的,因此,沒有明顯地加以推卻。實則,我學養未足,所知不多,又那敢在他面前放肆,為人講説佛法?豈料大約暑假末期,有一晚,他忽然偕同容君智寶親臨寒舍,將他剛編寫的一份佛學稿本交給我,謙説請我過目修正,他準備以之作為初階班的講義,並誠懇地再請我和他合講。法師的光臨,使我極感意外;法師的謙厚誠摯,更使我非常慚愧感動。我還怎可以推卻他呢?惟有勉力而為,毅然負起助講的義務。
是年十月八日,明珠第一屆初階班正式開課,學員眾多,擠滿全社,這都全憑法師的號召力。開課後,一切進行順利,法師很感安慰。就在這時候,他的腹腔毛病又發作,為了徹底治理,他準備入院做手術。十一月二十六日,佛學班上課至第八次,由他講「四大皆空」。下課後,他便隨著入院。入院時,精神還是好好的,我以為他做過手術後,很快便能出院復講,萬萬想不到,醫生手術不靈,九天內連做兩次,竟奪去了他那寶貴的性命!當時,隱盫先生、容君和我都守候在他的身旁。對他的遽爾去世,容君之傷痛固不待言,隱盦先生和我也都感到晴天霹靂,無限哀傷!諸行無常,從法師之匆匆離去,我有深刻的體會!
五 斯人不在高風長傳
直至法師去世後,我才從容君的口中得悉,法師對我厚愛,原來是因為他認定與我有一段往昔因緣。他在手術前告訴容君,三十多年前,他在廣州一佛學院任教,班中有一年青學僧名慧海,勤懇好學,又能接受他的思想,課後每留下向他執經問難,不願離去。可惜,沒有多久,慧海得病不治,臨終時,堅決要請法師到病榻前見最後一面,並對法師許下一願,願來世再與法師繼續此段因緣。也許法師有宿命通,又或因慧海有此臨終一願,而我與慧海又長相近似,年齡吻合,所以,法師便認定慧海即我之前身吧!總之,因緣是很奇妙的!
自法師去世後,明珠在隱盦與道生兩位先生先後領導之下,社務得以穩步發展,而佛學班亦賴以繼續開辦,以至於今日。我敬仰法師為教為法之熱誠,復感念他的知遇之恩,十八年來,在社講課不輟,以落實他的遺志。在發揮教義方面,我雖不如他那樣極力「破邪」,但卻也追隨他的思想路向:緣起──性空──中道,「顯正」不遺餘力。(破邪顯正是法師弘法的旨趣。他曾書此四字橫幅,筆力遒勁,現懸於社之當眼處),因為據我理解,這確是佛法中最不共世法的第一義。法師以中國佛教真常之教為邪説,我從佛教發展的史實中,卻看到立根緣起的佛法,就不同的時、地、人中流布,無可避免要増減開闔,容受變通,以求適應的方便。緣起之法,固應如是如是,只要是佛法,雖然不屬第一義,也總還有導向解脫的成份與作用,即此便應有其相對的價值。基於這個見地,明珠開設的課程中,有印度佛教史,也有中國佛教史;有成實、維摩、法華、般若、中觀等經論,也有俱舍、彌陀、唯識等要典,以求學員能抱持平實開放的態度,從兼學佛法的真實與方便中,得到最大的受用。
法師去世已十八年了。這麼多年來,明珠一直都堅守他的三不遺訓──不向社友以外的人士募捐;不主動邀外人入社;不做任何法事以謀利。很多學員因為喜歡明珠的作風,皆自動申請加入為社友,不少並成為得力分子,這都是法師的精神在發揮作用。
法師生前矢志改革佛教的弊陋,不惜捨棄既得的地位名利,從零開始去建設明珠這個清淨的小天地。雖然當時了解同情他的人不多,但他從身體力行之中,已滿了自己的志願,並對後來者產生深遠無窮的影響。這可説是所成者小,所化者大。由於他的言行類多反傳統,教界難免有目之為怪異、狂妄,甚至進而視明珠為地獄,但憑我對法師的真切認識,我很可以肯定,他的所作所為,所思所想,其實是合乎理性,忠於佛教,足可代表佛教的良心。「君子每為人記念,道風長與水流傳」,每當感念法師的時候,我很自然便記起這副由法師書寫,懸掛於明珠講室前的對聯。相信凡認識而了解法師心志的人,都有同樣感受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