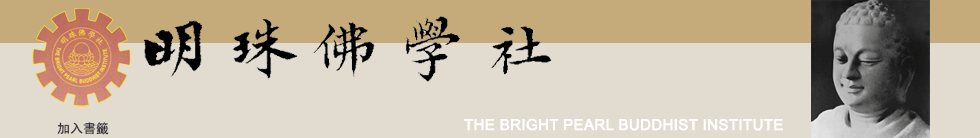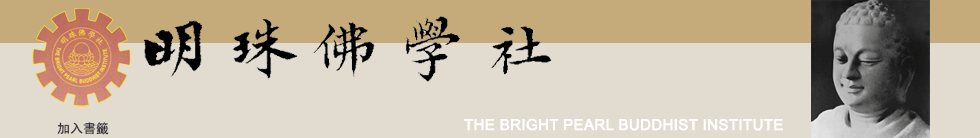—— 記故社長梁隱盦先生二三事
隱盦先生於一九八零年辭世,距今不覺已十年了。此十年中,明珠各方面都有所興革,社友人數穩定增長,經濟情況漸見好轉,而佛學班長期開辦,修業學員有增無減,這是先生住世時所逆料不到的。記得七十年代中期,明珠因佛學班學員漸多,地方越來越不敷應用,社友乃有遷址之議。其中尤以當時執委今社長之陳道生先生主張最力,但身為社長的隱盦先生對此議卻有所保留,懷疑社友是否有此財力,更擔憂明珠將來之經濟負担不起。不過,由於眾議所決,明珠終於一九七八年遷往冠華園現址。他對此事始終不以為然,直到病重住院,有一次去探望他,他仍然向我表示了心底的憂慮。但事實證明,明珠遷址以後,社務反為蒸蒸日上,他的憂慮是不必要的。
隱盦先生處事踏實,為人謹慎,這是他不願意遷社的原因之一。但更重要的原因,是他當時正主持孔聖堂中學的校政。孔聖堂中學當日為一所以孔道立教的私立中學,而隱盦先生平素除弘揚佛法外,最大抱負就是振興儒學,存續國粹。所以,自一九六七年出掌孔聖堂中學後,即殫精竭力,不休不眠地為該校謀劃建設,剔決頽滯。課餘並開辦國學研習班、中英繙譯班,以及徵文詩詞對聯等活動,另出版《孔道專刊》。繁劇的校務,已使他很難再有精力去擴展明珠,加上多年來他都是氣病纏身,此時因工作過勞,病情益惡,要兼負遷社重任,就更為困難了。幸好這件事得到道生先生協助策劃進行,終能順利成辦。
弘揚佛法,提倡儒學,是隱盦先生教育事業的兩軌。從一九六二年,他担任三輪佛學社佛學班講席開始,他就一直全心全力教導後學,永不言倦,直至嚥最後一口氣。那年,我參加三輪第一屆佛學班,開始修習佛法,也從此認識隱盦先生。他每次講課,總是一句緊接一句,滔滔不絶,如江河之傾瀉,奔流莫之能止。原定個半小時的講節,往往延至兩個小時或以上,他才肯停下來。看他講解的急逼、神情的著緊,就像是要於一課時間之內,將所有要教的都盡講似的。那時,他的氣管已有毛病,講課中常咳嗽大作。他這樣竭盡氣力的講課,其實是很辛苦的,也明顯會損害身體健康,但他自己卻毫不在意。後來,他出任孔聖堂中學校長,夙夜勞瘁,身體一年比一年弱,發病的次數也越來越多,但他並無懼意,反而更為勇猛,除了在校政方面大事興革外,於課餘更為孔聖堂陸續開辦國學班、繙譯班、哲學班。在去世前幾個月,他還在病榻中親自籌劃新一屆國學班的一切事宜,到開學禮那天,更堅決要帶病主持開學禮,上氣不接下氣的對學員訓勉。他對教育的熱誠,真是至死不渝的。
還有一件事,可見隱盦先生對教育的熱心。一九六八年,我和好友黃君有感不少小六學生升中試後或由於成績欠佳,派不到中學學位;或由於家境困難,無法繼續學業,從此便要輟學,踏進社會工作,實在可惜。乃籌劃創設一所夜中學,學費每月只收十元,讓他們無論在時間或經濟上都可以付得出。在課程方面,則特別重視中文及德育──中文科多了詩詞及應用文,德育課包括公民與倫理。我把這辦學計劃告訴他,請他出任校長,他不以我們的計劃為陋,一口便答應了,而且還親自和我們四處去找校舍。由於我和好友當時都只是收入微薄的小學教員,大家的家庭負担又重,憑兩人的捐資,是難以應付辦學的經常費用的,難得他在這方面也慷慨承諾,每月資助二百元。在那個年頭,二百元對一個受薪的私立學校校長來說,已不是一個小數目了。後來我才知道,他那時候在經濟方面正處於困境,如非對教育懷有一顆赤誠的心,又怎會這樣出錢出力去幫助兩個窮小子做一件不會得名,却肯定失利的事?可惜,辦了不到三年,原租用的日間中學停辦了,我們再找不到租金相宜的校舍,夜中學只好也跟著結束,辜負了他支持的美意。
隱盦先生雖然熱心講學,但明珠的社友與學員卻少有機會得聆他的教益。並非他不願意講,而是每次他在明珠講課,如果是一次便完的還可以,要是連續性的,則不到三次,他便會病倒。早期如一九六八年,社長明慧法師為社友開設夜間進修班,隱盦先生負責講國文,講了兩次,便因病不能再講,由法師接替。後期如一九七八年,明珠開辦第三屆初階班,他興致勃勃的提議依照中學佛學科課程編寫講義,並準備分担其中部分課題。豈料開課後他的健康情況便越來越差,終未能參預講事。他在明珠講學的因緣如此不順遂,明珠的社友與學員真是沒有福了!
隱盦先生自從學佛以後,即立願廣布法施,對邀請主持佛學講座者,從不提出任何條件,只求能盡心弘法。他子女眾多,又皆成材而能孝養,本來很早便可退休,安享餘年,但他始終孜孜矻矻,奮力不懈,為責任、為理想、苦幹到底,直是吐絲春蠶,到死方歇。如隱盦先生者,實足為後輩矜式。
(轉載自 1990年《明珠佛學社成立二十五周年特刊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