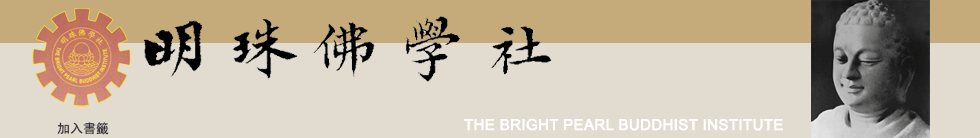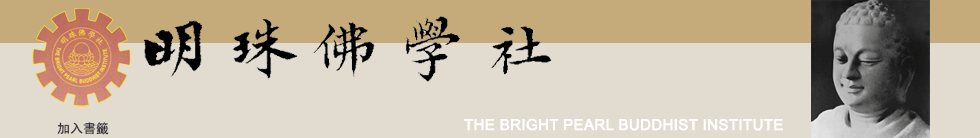(一)前言
西元前後,大乘佛教於印度興起,般若系經典從這時候開始便陸續出現。這些經典中最早傳來中國的,是後漢支婁迦讖於一七九年譯出的《道行般若》。其後四百年多間,繼續傳出的尚有《大明度》、《光讚》、《放光》、《大品》、《小品》、《金剛》……等多部。到七世紀,唐玄奘法師從印度帶回完整的大本,譯成六百卷,名為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。全經共十六會(這顯示般若系經典前後經過十六次之編集)。其中第九會,編列於第五七七卷的,名能斷金剛分,便是今日大家所熟悉的《金剛經》。連同玄奘法師的譯本,本經前後共六譯,今日最為流通的,是譯於四一二年的鳩摩羅什的譯本。
《金剛經》梵本三百頌,頌數與第十會的理趣般若同,二者同是十六會中篇幅最簡短的。由於篇幅不多,又能顯示最上乘的無相深義,更加上經中又處處讚歎讀誦受持的功德,本經自羅什法師譯出後,即受到佛教界的重視,普遍得到信眾的崇信念誦。天台宗的智顗、三論宗的吉藏、禪宗的牛頭法融,都曾注疏本經,就連唐玄宗皇帝也為本經作注,可見本經在當時流行的盛況。此外,禪宗自達摩開立以來,一向以《楞伽》印心,至五祖弘忍,則除了《楞伽》,還重視《金剛經》的教學。六祖慧能更由此經而得道。此見於《六祖壇經》行由品所載:慧能在未參禮五祖以前,聞買柴的客人誦此經,「心中開悟」,後往黃梅參禮五祖,五祖為說本經,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句,慧能即大悟,由此得傳衣法。慧能弟子神會於北方傳法,尤特別推重本經,認為此經「最尊最勝」見《南宗定是非論》卷下,《神會和尚遺集》引。
(二)空與假名的意義
上面提及,慧能由聽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而大悟。這句經文,顯示了《金剛經》的一個重要義理。依《般若經》,一切法(即事事物物)皆由因緣和合而成,並無實自體。它們是剎那變動的。主觀心識所能認知的,是事物於某一時空下所呈現的性相(性質與相狀)。這性相並沒有實在不變的成分;它隨時空之變而變,也隨構成它的各種因素變異而變。所以,一切法都是約制性的存在——受眾緣所約制,其存在便非實體性的存在。反之,它是變幻性的,是無自性的存在(自性即獨立而不變的本性)。因為沒有自性,事物的存在便兼具兩種性質。其一,它有和合而成的假體,而有體(雖然是假體)即有相、有用、有屬性,所以它非無。其二,它沒有實體,不能獨存,受到約制,剎那都在變動(此即念念生滅),所以又非有。非有非無,矛盾而又不相妨礙,這就是一切法存在的真相,又稱實相,也是世間的實際。但世間人沒有般若正見,觀察事物,不是認為實有,便是認為實無,由此而起的概念及語言,也就無從與實際相應。般若經為消解世間人對有無的偏執,所以設立「空」的概念,使世間人免於有無執見的糾纏,從而得以自有無的範疇超越過來,而悟證世間的實際。
「空」的意義有兩重。第一重,一切是無自性的緣起,所以沒有實自體,不能以世間人的經驗語言套上去,說它「有」,故說是空。第二重,正由於一切法沒有實自體,一切法才具可變性、和合性、壞滅性。既可變,可合又可滅,一切法才會互相架構,彼此成就,以及無常過轉,而於無常之中又相續不已。所以一切法亦不能以世間人的經驗語言套上去,說它「無」,而只可點出其無常而相續的存在為空。於此可見,空不但有消解作用,而且還有建設的意義。它顯示了因緣生法的狀態,與世間的實際相應。
但空也只是一個概念,絕非有一空性或空相真實存在,由它而產生一切法。「空」這一概念的設立,只為使世間人離有無的妄見。它是一種施設,一種安立的名字,佛法稱之為假名,空如是,其它諸法亦莫不如是。因為正如上面所說,世間的一切雖無實體,但緣生的假體仍是有的,這假體概念的獲得,是主觀的心識向外投射的結果。而由此獲得的概念是充滿主觀色彩,亦即是充滿情執的,在這方面說,世間是一個概念的世間,也就是一個名言的世間,《般若經》認為這種種概念名言只屬隨宜安立性質,並不能代表世間的實際。所以便稱之「假名」。緣生的一切法,因為沒有實自性,故說是空的,也是假名而有的。緣生、空、假名都是對世間的如實觀,都說出世間的真相(實相)。
所以,《金剛經》處處有這樣的開示:說XX,即非XX,是名XX,(如「說是一切法,即非一切法,是名一切法」)。第一句舉出世間人認為有的法。這二句指出這法其實是虛妄不實的(因為一切法由因緣和合而生之故)。第三句開示法雖不實,但不礙其有緣生假名的體及作用。也所以,本經說「凡所有相,皆是虛妄;若見諸相非相,則見如來」。一切相,無論器界、眾生界、或色、心諸法,都是無自性的存在,都是虛妄不實的。如果能夠對此作如實觀,見諸相的不真實,即見諸相為非相,便可不著一切相,離一切相,而悟入無相。這就見到世間的實際(亦即實相),直契如來的本懷了。本經以無相為教,其實就是要學者徹悟諸法的實相。
(三)緣起性空心不住
明白了上述般若經所顯示的空與假名的意義,就可以了解《金剛經》所說的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的深義。「住」,是黏著的意思,指主觀的心識向外境攀緣的時候,所生起的錯誤執著。前面說過,主觀心識所能認知的,只是事物於某一時空下所呈現的性相,這本來是無常而相續的假體存在,但世間人沒有般若正見,當心識攀緣外境為對象時,便執對象為實有或實無,而不能與緣起念念生滅的實際相應。所以,常人於心識起處,即生迷執,而成過患。但人非木石,不能制心令其不動,以求免於過患,故《金剛經》教人,心儘可生,但不要住於相,不黏滯於一切法上,虛妄的還他虛妄。這樣就不會像常人那樣,在見色聞聲時,以為色聲的本質就如現見現聞的這樣,而生起迷執,成煩惱之源,生死之本。「生其心」是主體接觸客體的活動,屬於緣起邊事;「無所住」是主體了然於客體的不實在而還他個不實在,達致主客無阻隔,這屬於性空邊事。凡夫不見緣起,故生心而住,住故煩惱、生死;聖者正見緣生諸法空,故生心而不住,不住故清淨、解脫。修行人若能通達緣起不礙性空、性空不礙緣起,就能生其心而無所住,轉煩惱為解脫了。
(四)般若實相畢竟空
禪宗以《金剛經》為教,就是要藉著般若正智,蕩除主觀心識的情執,使心識於緣外境的時候,不生黏滯,從而直見存在的真相。不過,禪宗所說的實相,是真實自性、是如來藏,是真心。這是眾生原本自具的,只因眾生著相起執,才迷失此本具的真性。通過般若的掃蕩情執,真性就可呈現。所以,慧能於大悟後,隨而對五祖說: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,何期自性本不生滅,何期自性本自具足,何期自性本無動搖,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」。這個原本就清淨恆存,無為而能作萬法根源的自性,就是如來藏,而五祖座下另一弟子神秀所說的偈語:「身是菩提樹,心如明鏡台」,以菩提樹、明鏡台喻身、心,亦可說明禪宗是以如來藏作為眾生存在的本源的。在這方面說,禪宗是離開般若經的宗旨的。般若經說的實相,是一切法緣生緣滅,無自性空的實相。如前文所引,見諸相非相,才見如來。見如來就是見實相。一般佛教學者以為《金剛經》所說:「一切有為法,如夢幻泡影,如露亦如電,應作如是觀」,是指有為法虛幻不實,無為法仍是真實而有體的。不知道無為法是因眾生執著有為法而說的,也是一種施設。於有為無所取,無所住,當下便悟入有為的實相,而假名之曰無為。所以《大智度論》說:「有為法實相即是無為……若分別有為法、無為法,則於有為、無為而有礙」(卷三十一釋初品中十八空)。實相是並非離一切法而別有實體的。般若經十八空中,有「空空」,「空空」即「空亦復空」,說空空,就是恐防學者執空成見,以為實有空性到底不空,而由空性生萬法。《金剛經》也說:「知我說法,如筏喻者,法尚應捨,何況非法」。修行人到徹悟的境地時,是對一切法包括有為與無為、世間法與出世間法、生死與涅槃都無所執取的。這就是「般若將入畢竟空」的道理。
部分佛教學者認為,眾生能夠由凡夫成佛,在主體上應已有一清淨本性,才可藉福智因緣,轉穢成淨。否則,染穢的凡夫如何得以成清淨圓滿的佛。對此,《大般若經》卷550第四分深功德品有很好的開示:經中善現(即須菩提)問佛,菩薩修行,是如何積集善根,證入無上正等覺的呢?佛先舉燃燈為喻:燃非只出初焰,但亦不離初焰;非只由後焰,亦不離後焰。就是前後焰無常而相續,燈便燃點起來。故「諸菩薩摩訶薩……非初心起能證無上正等菩提,亦不離初心,非後心起能證無上正等菩提,亦不離後心,而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,方便善巧,令諸根增長圓滿,能證無上正等菩提」。眾生能夠成佛,就是在無常而相續的緣起法中,不斷精進,長養善根,積集資糧,轉惡為善,轉善為淨,也就可以由凡夫至賢人,由賢人至聖者,其間純是一個轉化的過程。而轉化之所以能夠完成,就因為一切法是無自性空。若有實在不變的自性,則凡夫是凡夫,聖者是聖者,兩不相涉。同時凡夫亦只可有凡夫性,不應凡夫中有佛性,否則便是一體而有兩種不同的實性,矛盾而相妨礙了。
回過來說,禪宗是以說如來藏的《楞伽經》印心的、《金剛經》則非用以印心,而只是作為去除妄執的一種修行上的方便法門而已。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,「無所住」,在禪宗只是一種方便,藉無所住而顯現本具而恆住的如來藏。在《金剛經》則至於聖境仍是無所住,那就不單是方便了。
(說明:此文章所有版權屬原作者所有,本社感謝作者提供文章於此平台與大眾分享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