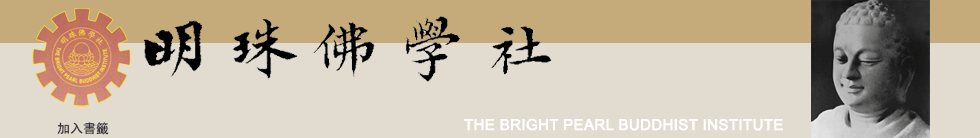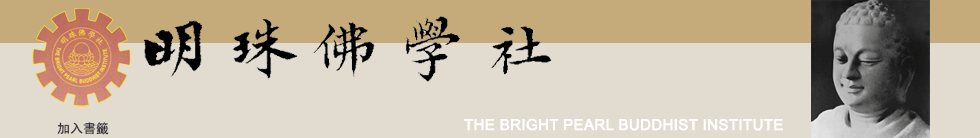《金剛經》梵本三百頌,漢譯一卷,是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六百卷中的第五七七卷,十六會中的第九會。它的頌數與第十會的理趣般若同,二者都是十六會中篇幅最簡短的。本經前後共六譯,今日最為流通的,是譯於四一二年的鳩摩羅什的譯本。本經由於篇幅不多,又能顯示最上乘的無相深義,更加上經中又處處讚嘆讀誦受持的功德,自羅什法師譯出後,即極受到中國佛教界的重視。各主要宗派如三論、天台、唯識、賢首,以至禪宗,都有對本經的註疏。禪宗的五祖很重視本經的教學,六祖慧能更由於聽五祖講本經,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而開悟。慧能弟子神會於北方傳法,更特別推重本經,認為本經「最尊最勝」(見《神會和尚遺集》引《南宗定是非論》卷下)。
本經徹底破除一切執著,包括對佛身及佛法的執以為實,極顯人空與法空。 所以說「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….如來所說身相,即非身相」;「凡所有相,皆是虛妄,若見諸相非相,則見如來」;又說「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、不可說,非法非非法」;「所謂佛法者,即非佛法,是名佛法」(羅什譯本缺「是名佛法」一句)。這是因為一切法都是眾緣所成,無自性的存在。其存在都是依存性的,故皆虛妄不實,便是出世間法,也是相對於世間法而施設。沒有世間法,也就沒有出世間法;有世間法,才有出世間法。所以,本經教菩薩作事,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,「生其心」,是起心動念,是主體接觸客體的活動,此屬緣起邊事;「無所住」,即無所黏著,是主體了然於客體的不實在,而還他個不實在,達至主客無阻隔,此屬性空邊事。這是說,心儘可生,事儘可作,但要不住於相,不黏滯於一切法上,虛妄的還他虛妄,離相無住,就是解脫的境界。
上面所簡述的本經經旨,全經處處透露,清楚易知。可惜歷代本經註釋,或偏重名相典故的疏解,陳陳相因,支離雜遝,與本經精神不相應;或將有為無爲,世間出世間法打成兩橛,以有為、世間為不實,無為、出世間為真實,用有見裁空義,乖離本經的宗旨,如唯識宗的窺基撰《金剛般若經贊述》(兩卷),依無著世親的釋論,解「所言一切法,即非一切法,是故名一切法」,說「言一切法者,謂佛所證法;即非一切法者,非餘人所得法,或非分別之相法也」(卷下)。將一切法分為佛所證法,與餘人所得法或分別之相法兩類,因此「彼(佛所證)一切法,便不是此(餘人所得或分別之相)一切法。(是名一切法未見解釋)。但經意第一句說緣起,第二句説性空,第三句説假名。這是從不同角度去看一切法,並非有兩類不同的一切法。基師所解,全沾不著邊際。又解「如來說莊嚴佛土者,即非莊嚴,是名莊嚴」,説「如來説莊嚴者謂無相之莊嚴;即非莊嚴者,非有相之莊嚴;是名莊嚴者,是真實莊嚴也」(卷下)。這種解釋,亦犯了上述同樣的過失。這都是看出世間、世間法為截然不同的兩回事,有乖《金剛經》經義。又如三論宗的吉藏撰《金剛般若疏》(四卷),解「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,如人入闇,則無所見;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,如人有目,日光明照,見種種色」,説「雖常有真如佛性,心無所住則見,有所住則不見也。顯性之言,事在斯也」(卷四)。菩薩非佛,豈能説「常有真如佛性」?因地為菩薩,證果才成佛,若菩薩而有佛性,那就犯了因中有果的錯誤,而且上述的解釋亦不符合經意。又解上面一切法那句,説「即非一切法者,一切顛倒之法,此非如來所證……是名一切法者,還結一切法如也」(卷四),其誤亦同基師。除此,吉藏的疏解更喜於名相支節上無端糾纏,如解經文第一節,講乞食的種種利益作用,去了六百多字;講比丘所穿衣的種種顏色剪裁功用,去了八百多字;講缽的不同容量,又用去三百多字。這樣支離雜遝的疏解,是不少金剛經註釋的通病。而像吉藏、窺基那樣以有見裁空義,就更是歷代大部分註者的共同過失。這種過失對研習般若的學者來説,是致命的,因為他們循此以學,終不得《金剛經》性空中道、離相無住之旨。
明慧法師講解《金剛經》則完全沒有上面所舉的兩大通病。他的講解以中觀家的洞見,直入般若的畢竟空,由畢竟空而全得本經離相無住的經旨。下面略舉法師所説,以作印證。
本經處處有「説是XX,即非XX,是名XX」的話,這是開示「一切法是緣起無自性空,而假名的體與用非無」的般若要義。由這義理,可悟解從緣起中才見畢竟空,畢竟空中才無礙緣起的深義(若有法不空,就不成緣起了)。一般疏解能達此意的少之又少,如上舉吉藏、窺基的疏就全不是這麼一回事。法師解此,則説「明白一切法無實性,即非一切法,但以假名字説,故是名一切法,能通達此三句語法,即是四句偈,即通達般若波羅蜜,通達空理」,隨引《中論‧觀四諦品》的「三是偈」為説。這首偈正是闡明緣起──性空──假名的最好論證。 只有般若的會家,才會以此偈去比配《金剛經》的「説是XX」等三句。這比配是何等貼合,又何等切要!又如本經説的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,是經中佛教菩薩日常修行的要訣,非常吃緊。法師解此,説『小乘人見有色而心不住色 ….大乘人則明白色本空,無色可得,故不住色….小乘人見有而不去著,大乘人了達其空而不著。「應無所住」就是明理,「而生其心」謂之做事;「應無所住」為般若,「而生其心」便是方便。有般若有方便,如此方為菩薩行』。短短的説話,不用典,不引文,只是直入直解,就將經意清楚解釋,並連帶説出大小乘人解空與不解空所造成的境界差別,以及菩薩須兼有般若與方便的這一特性,而解釋亦因此更圓滿。類此的直入直解,通篇如此。般若甚深,所以解般若最難,而要深入淺出去解説更是難中之難,但法師卻做到了。他解經一向不用科判的方式,就是要保持他的單刀直入的解説方法,避免學者徒勞於章節架構,反不易得經意。
有一點尤須特別指出,中國傳統佛教,無論空宗有宗,大多將有為無為,世出世法截然分為兩橛(如前文所説),而偏執最後實體、實法為有,為不空。便是解般若亦用此見。故本有佛性、真心不滅之説,縱非教界的共識,亦為多數宗派的主流思想。明慧法師解本經,則直探《般若經》的核心,揭示般若的畢竟空義,完全不受傳統思想的羈絆。所謂「畢竟空」,即並非部分空,部分不空,而是無一例外的一切皆空。所以,不但有為、世間法性空,無為、出世間法也同樣性空。 這對大部分講本有佛性、真心不滅的學者來説,是很不易了解,也極難接受的。 法師於此,則慧解處處,不落前人的窠臼。如解「實相」,説「所謂實相 ….其實即是非相,非相即是空,無實體性。如來但以假名説為實相,實相只為如的義理,佛亦不許可執著此義理為實有的」;解「凡所有相,皆是虛妄」,説「凡指概括一切世出世間,十法界皆是虛妄假有,這是從因緣性見其虛妄」;解「如來所説身相,即非身相」,説「凡有皆是因緣有,相對有,假有 ….世間法如是,出世間法亦如是,佛亦如是。眾生空故,佛亦空。所以不能執著有佛之見」;解筏喻,説「筏只為過河之用。渡河後便要捨棄。空理亦如此,乃借用之道理;將空理破不空理,破得不空理之後,則空理亦不應執著」。這類慧解,求諸傳統的疏釋,是不可得的。
回想廿六年前,與法師初相識,他就對我一見如故,視我為忘年之交,在佛法方面,常作耳提面命。當時我已學佛數年,走的是傳統的老路,對《楞嚴》尤其歡喜。有一次,我花了多天工夫,根據圓瑛法師的楞嚴講義,列寫成長長的一份科判,請他過目,以示學經不懶。怎知他看也不看,臉色一沉,隨著就對我細説傳統佛教思想的不如理之處。以後,他便常常在交談之中,為我介紹印度原始佛教與大乘般若的義理。雖然交談是東一句,西一句,不循次序系統,我已從中得到極大的啟發,離開老路,從零開始,去探索佛法的源流演變。事後回想當日的情形,就有種脫胎換骨的感覺。如果當年沒有得到法師的寶貴啟引,相信今日我對般若的深義當無從索解,也就沒有可能説出法師這本發微有什麼特別的地方,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價值了。
如今,藉著本書的出版,特說出我對法師的慧解之所見所得,以稍報他當日啟導之恩;同時也好讓有意參學般若的善友認識有這麼罕見的慧解,而知所珍視,好好地加以研習。那麼,我雖多費了篇幅,相信讀者還是會原諒吧!
黃家樹序於加拿大多倫多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九日